邹羽|《狂人日记》的文本空洞
——兼论论鲁迅小说的语言自我和心理主体
文/邹羽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叙事文学纪念碑式的源头,但它也是现代中国叙事的一个不可能的源头。[1]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它以从崩溃到康复的样式把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在崩溃和康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亦即在病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之后,到身心“痊愈”,“赴某地候补”之前,故事造就了巨大的文本空洞。这个空洞充满内容,却无法用语言表述。如果说故事正文所表述的越陷越深的幻觉只是丧失自我的前奏,那么区隔故事正文和故事序言的这个无语的空间就是疯狂的顶点。在那里,就连狂人的幻觉都已消失,因为作为幻觉支撑点的具有言说能力的自我——也就是语言中作为主语的我——已经彻底崩溃。狂人丧失了最后一点与人交流的能力,和在客观世界中的锚定效能,从而完全陷入奔涌倾泻的主观感受之中。当然,日记作为自我对话的一种文体,在开端就体现出对于任何一个外在于自我的交谈对手的有意无意的忽略。语言能力的崩溃,正是主观感受取代外在世界的极端表现。
就鲁迅这篇作品本身而言,无语空洞的作用非常明显,在标示出病人疯狂的极限状态的基础上,它为作品叙述的完整性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同时它也为后人提出了问题:究竟谁是狂人话语的承担者?究竟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幻听幻视症状日趋严重的言说者(ego)身上?还是需要更加重视那个在疯狂言说者背后的那个最后失去语言的经验主体(subject)身上?因为两者间显然不是互相置换的关系。也许由于我们大多数心智正常的批评家和阅读者对于疯狂的经验总是局限于浅表,所以即便《狂人日记》中的无语空间以这样显著的方式出现,从五四到目前对于这篇经典作品的评价中,它常常被排除在论题之外。正如法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医生拉康所说,对于疯狂,我们一般以深度阐释为标准的理解活动是起不了作用的。疯狂的意义太过直白。只须指出“他疯了”,阅读就此停止。对心智正常者而言,不是说在主观上引导自己疯狂,就能进入疯狂的状态。[2]除了疯狂者本身,疯狂无法经验。而疯狂者语言能力的丧失,也使得这种经验无法传递。一旦我们仍然希望理解疯狂,那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理解对象假设某种虚构的深度,从而也使理解活动从起点就走上歧途。那么今天如何理解这篇五四经典中,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构成的基本状态和条件,或者说中国文化主体的古今之变,亦即传统到现代的转折,也就成为对一般读者和知识人的根本性挑战。华裔学者李欧梵曾经声称不读鲁迅就是文盲。而对于任何一个参与讲述现代中国经验的文化人来说,不能厘清《狂人日记》这一源头文本的内在困境,我们对自身所从事活动的认识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当然,在讨论心理叙事对中国现代文化构成的挑战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精神分析在五四后中国的普及历程,因为正是由于这一学说的大力倡导,现代学术才把文化活动中的心理内容与其他历史内容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人文研究的独立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对象。弗洛伊德学说传到中国,恰巧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步。1919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的汪敬熙就在学生刊物《新潮》上介绍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有关精神分析的一系列辩论。1921年,罗迪先翻译的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其中也包括对弗氏学说的介绍。1929年章士钊与弗氏本人的通信,以及他在次年翻译出版弗氏1924年所作的《自传》已成为中国精神分析学界的奠基性事件。[3]而高觉敷1930年初版,1984年又一次隆重推出的《精神分析引论》译本,更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逐渐进入了一般读者的视野。[4]然而,尽管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前哲学思想和文化解析模式,在弗洛伊德生前就在西方取得了广泛影响,而且从五六十年代起,拉康学说的兴起,以及它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流,更使之成为几代人文学者的基本学术取向和分析词汇的来源,它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说一直处于文化和学术的边缘地位。从在五四高潮时期提倡西化的胡适,到在八十年代推动译丛的甘阳等人,居于学术话语中心地位的文化领袖给予精神分析的关注微乎其微。虽然1984年高觉敷译本重新出版,但作为弗氏学说二战后最重要革新者的拉康已经在1981年作古。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在后者以及阿尔图塞、克里斯蒂瓦和米勒等同道和追随者手里,精神分析以及它对人文研究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东欧左翼学者齐泽克在拉康和黑格尔两者论述之间作出的大量阐释,,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学界汇合精神分析与德国古典哲学两种思想传统的风气,虽然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是对黑格尔的过度评价,以及对拉康的评价不足,从而牺牲了老派法兰克福学者所强调的、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哲学和的非传统性。[5]
本文的工作,是希望从鲁迅小说直接呈现的心理体验出发,讨论五四叙事中真实世界的极端不稳定性,从而重新检视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特殊构成条件和本原性挑战,从而为从鲁迅研究出发,探究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半殖民地经验,以及对于源自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现代性本身的一般意义,作出一些话语铺垫。虽然自启蒙时期的卢梭一流人物开始,心理体验作为现代的持续在西方语境毫无疑义,但只要触及殖民文化对全球文化现代性的构成性影响,即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具有指标意义的西方左翼话语,至今也只是在非常边缘的意义上对待非西方现代心理主体的生成这个问题。比如针对后殖民主义批判创始人法农的所谓“心理主义”的淡化处理就是一例。[6]似乎非西方社会针对殖民影响的文化对策具有心理上的扁平单一性,或者说殖民地人群面向殖民历史的所谓心路历程本身就是病理性的黑暗体验,。就中国现代文化研究而言,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的半殖民地理论虽与当前西方左翼话语尚有距离,“去心理化”的基本取向。[7]这样的取向甚至在国内人文学界从总体上背弃列宁主义影响的改革时代,仍然发生着一定的作用。而笔者秉持的、所谓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经验不能仅仅还原为政为治经济学分析的立场,当然不仅仅是一项纯理论干预。它同时也在回应全面工业化所造就的中国社会日益波澜诡谲、雄浑深厚的心理现实。可以说,从牵涉人群的宏观量级及其孕育速度而言,这一现实对于全球化过程中、以西方为中心的片面工业化现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以西方为中心的片面工业化本身,可能正为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文本的扁平化解读和反向深度自我构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并使得非西方必须通过西方阅读自身。
《狂人日记》版画,赵延年绘
自其诊疗生涯的早期,弗洛伊德就试图从临床角度解释工业化社会人群对于真实世界的病理性回避。在1911年题为《心理功能两项原则的表述》的著名短文中,他更把神经质疾病(Neurose)和精神性疾病(Psychose)的异同归结为如下情形。[8]由于心理活动的根本原则是趋乐避苦,心理主体一旦在真实世界遭遇痛苦,就会把关注力投射到与真实世界相反的方向。如果投注对象是幻想世界,而主体同时并未否认真实世界的实在性,这就是神经质疾病的基本状态。在其它场合,弗氏还将此状态描述成自我(Ich)与本我(Es)之间的对立。但如果主体对真实世界的回避达到极端,或者它已沉浸在与真实世界高度背离的幻觉世界之中,那么神经质疾病就发展到精神病阶段。在此阶段自我和本我相互联合,共同对抗真实世界产生的压力。用经过后人整理的语汇加以表述,也就是说,从一方面来看,神经质疾病体现为心理主体对真实世界的压抑(Verdrängung),而从另一方面看,在精神类疾病状态下,真实世界已被屏蔽在心理主体的主观感受之外(Verwerfung)。在针对关注力投射的论析中,弗氏特别延用了Besetzung一词军事占领或力量投射的本意,来指定心理能量对于某些观念,或人体的某些部位,或身外某些客观事物的胶着性依附。该词法译investissement,但是被英译者转成较为古奥的cathexis,意思反而变得晦涩。至于中文意译,笔者就本文语境看则以为“锚定”为好,因为在弗氏理论框架中,Besetzung的功用原本就表现为通过心理能量对有关客体的附着,来为主体心理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提供保证。虽然神经质疾患和精神类疾患同样与心理能量在真实世界中的锚定松弛和不足有关,并同样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锚定错位,但前者错位的关键是,心理主体将关注力特别投射到作为快乐原则减去现实原则所得之差的幻想空间(fantasy)之中,比如说常人失恋后通过幻想得到的替代满足。这样的满足并不说明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否定,而只显示出,相对于现实原则所重视的真假判断,快乐原则所依据的苦乐感仍起主导作用。所谓替代满足,也正是心理主体在认可幻想空间非真实性的条件下,对于心理快感的继续坚持。至于精神类疾患的锚定错位,当然就不再是自觉的幻想追逐。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遭受此类疾患困扰的心理主体,其现实原则已被腐蚀,其心理锚定对象也转向主体本身。重大的事实冲击,在后者往往造成感知过程与真实世界的完全脱节或者失锚。从病理内容看,当事人时常产生针对自身真实状态的根本性误判,比如经历某种自大狂幻觉(delusion),。
以鲁迅本人所谓“我一个也不放过”的残酷风格而言,他的现代文学开宗明义篇《狂人日记》,在某个意义上已经显现出它对于替代满足的强烈疑虑和反感。这样的疑虑和在后来的《阿Q正传》中得到进一步扩展,但从作者创作生涯和中国现代文学共同的开端来看,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冲击力度如此巨大,它使得叙事主体不得不以放弃现实原则并且屏蔽真实世界,或者说以全面陷入幻觉世界为代价,从而保护其心理结构的基本稳定。[9]当然如果考虑到狂人最终还是陷入疯狂失语状态,这样的稳定脆弱而短暂。作者对于冲击创伤的极度敏感及其在叙事操作上第一时间的天才处理,构成了他在以后生涯中批判阿Q精神以及在所谓中国国民性头衔下出现的一切替代性满足策略的话语基础,当然也为后来学人批判他对替代满足本身的片面理解提供了理由。显然,替代满足的全部内容并不局限在脱苦求乐,因为不论阿Q还是祥林嫂或其他一切等价值,在他们受到现实困扰的语境中,快乐原则得以持续的代价正是对现实原则的压制,所以幻想和自欺在浅表的快乐以外总是指向本原性的不安和焦虑。鲁迅对此类本原焦虑缺乏深入关怀,也使他至少在某个特定意义上由衷鄙视弗洛伊德医生眼中、现代社会纠缠在神经质疾病边缘的大多数人,或者说使他的文化干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启蒙或者宗教救赎。而同时,狂人在遭受巨大创痛之际,因为关注力必须聚焦于受创主体和创痛部位本身,以此造成他对于创痛体验的隔离和对于创痛源头的真实世界发生锚定松弛的反应,并且在幻觉世界里越陷越深。但这也并不意味其心理经验全然可以等同于痛苦,因为创痛源头的封闭也能给主体带来夸张的快感,于是主体的苦乐经验在失去客观锚定之后会进入巨幅而强烈摆动状态。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狂人热爱自己的幻觉如同他热爱自身。在感受幻觉带来的、超出常人所能感知的极度痛苦的同时,鲁迅作品的叙事者也获得了常人难以享受的无比清晰而且异常崇高的洞察力。启蒙的心灵,在中国不同于热情的卢梭和谦卑的康德,也不同于同治中国或明治日本的铁腕改革者。正因为现实原则急速腐蚀,鲁迅的狂人才能雄踞历史之巅,痛诉昊天不仁,睥睨过去现在一切众生,齐同巅峰狂喜和地狱绝望,把强烈的文化自恋激化为彻底的文化自毁,把意在长生久视的历史和文化规划简化为不顾一切的个人要求:救救孩子!如果幻觉世界必然在疯狂中走向毁灭,狂人自身也必然在疯狂中彻底消亡。persecution)的阅读,:村人的、大哥的、何先生的、李时珍的、二十余岁面目不清的、母亲的、自己的,站在其背后的并不是令人难以琢磨彻底的真实主体,相反它们的形象枯燥雷同,可以说仅仅是叙事者本人单一主体的不同面具。[10]这也证明在作品中意图食用,,并非狂人臆想中的他人而是狂人自己。“救救孩子”这项博爱呼吁的阴暗面,正是“我已无可救赎”绝望自恋。而回到弗洛伊德的语境,这正以自恋与自毁的在极端状态下的相遇重合作为例证,表明了锚定作用所同时具有的侵犯(aggression)和毁坏倾向,或者说心理锚定的原生不稳定性。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就叙事学一般结论看,与现代小说伴生的西方心理叙事,其操作原则是通过所谓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来展示一类此前专注于动作的古典叙事所不擅长表现的内在体验、以及由此类体验构造的内在世界,比如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感知。[11]多年前,Dorit Cohen还为这样的内在世界提供了一个琅琅上口的名称,即所谓“透明的心灵” (transparent minds)。[12]之所以透明,是因为它就像一个可以用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加以展示的、散文化的、亦即在纸面上书写、延伸、和虚构的心灵。而根据拉康对神经质和精神类疾病的病理学划分,此类游离于外在动作和外在话语之外、不能完全为其统摄的内在话语得以构成,它本身就由某种压抑所致,同时也与神经质疾病的原型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此类内在话语并不来源于心灵本身,而是来源于触发心理主体锚定危机的外在影响和外在话语。拉康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重新诠解为“他人话语”,并指出潜意识具有和语言同样的结构,用意也与此相关。当然,具体落实到心理叙事的语境,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心理叙事的内在世界,其根本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内心独白化了的角色对白。而作为现代中国心理叙事的滥觞,《狂人日记》重点表现的精神类疾病,它的工作原理就与上述“透明的心灵”全然相反。贯穿鲁迅叙事的始终,狂人心灵的透明度令人存疑。伴随对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透彻洞察,他对于本身从属的身边群落存在着灾难性的误读。虽然我们也许不应该简单地把狂人的现实视作“昏暗的心灵”,但至少也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奇异的透明心灵。同时,指出狂人的心灵缺乏一般心理叙事所设定的、在日常语言意义上的透明度,并不等于说现代叙事传统中的日常语言在此被诗化的非常语言(extraordinary language)所取代。相反,狂人内在世界的构筑材料,或者说日记本身的语言,与通常心理叙述所要求的日常语言并无二致。其非常性存在于一项狂人特有的病理症状:幻听。或者说,因为的外在真实世界已经塌陷,主导狂人内在经验的不再是经过心理压抑重新整理的他人话语,而是经过幻觉处理之后被误认作他人话语的自身话语。如果说欧式心理叙事的神经质结构(neurotic structure)是外在冲突内在化,或者外在动作的内在语言化,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把社会阶层和财产转移等社会差异转化为伤感的内心选择,那么中国现代心理叙事在发轫之初,就倾向于展示拉康所谓的精神病结构(psychotic structure),即是将内在冲突外在化,或者内在语言外在动作化,比如鲁迅狂人的一切遭际,都可定义为角色冲突化了的内心独白。换言之,与其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心理叙事作品,不如说它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理经验外在动作化的传统,提供了规范力强大的蓝本,当然这样的心理经验内容虽作为镜像令人印象深刻,但从语言符号上看却极为贫乏。狂人内心独白并不是诗的语言,它并不传递或建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新世界,除去错位感极其强烈的就事论事,它一无所有。然而目前学界针对心理叙事如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兴起的重要研究,比如刘禾老师早期的部分阐述,基本倾向于跟踪比如自由间接引语等话语技巧的采用,往往忽视了在现代中国在漫长的工业化初期,欧式心理主体在中国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以及《狂人日记》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心理叙事所提供的内在冲突外在戏剧化的长期替代性话语模式。[13]依据拉康区分神经质和精神类病患的原则,我们可以说造成这一误区的根本原因就是,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话语在基本策略上长期未能正视殖民创伤带来的文化失语危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本身作为在失语边缘构筑起来的话语体制这一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根本意涵就是,同时也将在失锚状态下必须投放到他人口中才能被心理主体听受和领会的语言本身,简单直接地当作所谓“吾手写吾口”的反心理表述媒介。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重新认识《狂人日记》,还有一个原因是弗洛伊德和拉康这两代哲人都曾经关注施莱伯的《关于我神经疾病的回忆》这部欧洲版狂人自述。[14]施莱伯是与弗洛伊德同时的一位德国高级法官。在他刚刚成功升任关键职位不久,曾经治愈的心理疾患再度突发,而且病情严重,被迫长期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开始撰写《回忆》,详细记录了自己种种迷幻症状,并给出怪异的理论加以解释。拉康正是根据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评判和自己的延伸阅读,从一个侧面发展出他的精神类疾病分析,以及他整套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15]如果我们把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当做一个整体,而且认为《狂人日记》叙事者的疯狂同样侵蚀了鲁迅作为短篇小说作家的身份角色,那么显然施莱伯从患病到撰述的过程也为患者把叙事这一手法当做自我治疗的首选提供了先例,而且鲁迅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几篇虚构作品,可以说几乎都在回应他首篇创作的灾难性冲击。正如《狂人日记》开启了《呐喊》序列,记述与狂人类似心理失锚体验的《祝福》正是他延续创作冲动的第二个出发点,并且成为《彷徨》序列的基石。[16]其中祥林嫂在丧夫、被、再度失去丈夫和儿子、以及自我救赎的努力一再失败以后,终于难以忍受真实世界带来的痛苦,陷入欲望的退缩(regression of desire)和对客体的去锚定过程(de-cathexization of objects)。她同时将心理能量病态地投射到自身,在自我怜悯(“我真傻”)和自我拆解(“死掉的一家人在,都能见面的?”)的重叠作用下,走进叙事者“我”所不忍直视、无从描绘的疯狂中。作为《狂人日记》故事的延续,祥林嫂的悲剧首先是她心理主体的死亡,而不是她肉体的死亡,正如狂人的黑色喜剧是他居然可以从疯狂的深渊中得到康复。显然,与《狂人日记》相比,《祝福》中的疯狂被外在化了:它不仅可以像狂人的经验一样被观察,而且更可以随着叙事视角伸展,被艺术性地赋予多重逐渐强化、意义明显的直接原因。相对于狂人,祥林嫂的疯狂具有确切的病源。仅就这个层面上,后者也为前者无缘由的疯狂提供了解释甚至治愈的方案和可能。当然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方案和可能,或者说为什么狂人的经验本身并未伴随这样的方案和可能,而解释必须通过迂回、延宕和艺术化的组织才能发生?在五四语境中,解释狂人的经验究竟可能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两篇故事的另外一重显著差异也值得我们加以重视。根据拉康的病理分析,精神病患者在幻觉日趋严重的过程中,因为现实原则的崩坏,其念兹在兹的不是事件的真实性,而是事件的肯定性。狂人不在乎社会上家族中母女兄弟相食的惨剧究竟是否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他只是在感情上知觉事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而且绝对不容他人置疑。而祥林嫂疯狂的起点正是她对于自我罪孽的全盘肯定。生活的苦难本身并没有把她从现实中剥离出去而使她走入迷幻(hallucination),做到这一点的是她在人生尽头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当作一切极端苦难的不可纠正的来源,和无可逃避的承受者。而两篇小说之间,鲁迅的匠心也得以施展。狂人确认一切人的罪,祥林嫂只是确认自己的罪。狂人像施莱伯呼唤上帝一样呼唤孩子和人世的拯救者,而且似乎把深陷罪孽的自身当作拯救者在人世间唯一福音传递人;祥林嫂的上帝,《祝福》中识字的出门人“我”,却不再沉默,而是直截了当地再度发出被她否定的声音:“地狱?——论理,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如果狂人还有上帝,祥林嫂在她陷入失语状态的前一刻,已经只剩下她自己。不过随着拉康的思路再前进一步,假设我们也认为所有对于真实的终极认定都包含所谓信心的飞跃(leap of faith),或者说都包含幻觉的结构(其实这也是尼采晚年论断的反话正说,即所谓最美好的心灵都处于癫痫状态),祥林嫂对于终极真实的幻觉认定就显得比狂人更为极端和强势,她不仅没有可能肯定自己幻觉世界的上帝,而且她罪止一身,不及他人。在视觉意义上,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把近景的狂人“我”改换为中远景的祥林嫂“她”,其释读和解决疯狂的动机可以说相当明显,但与此同时他扭结的天才也使得自己原本强大的释读变成徒劳,因为令人痛苦的真实甚至无关他人无关社会无关历史:在濒死绝望中狂喜的老妇人头脑里,它一闪即逝。《狂人日记》的文本黑洞虽然出现在作品结束之后,开端之前,但作品本身也是对疯狂的博物馆式的封存。《祝福》的情况有所不同:疯狂随着祥林嫂的死亡成为过去,它对叙事者以及文化主体的指责却永难闭合。就老妇人的身心崩溃而言,叙事无效。在鲁迅的小说家生涯中,它也同样指出,就狂人在历史洞察的巅峰突然陷入失语而言,叙事无效。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而我们面向《阿Q正传》的分析,也只有在明确了《狂人日记》和《祝福》两者关联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合乎病理逻辑的框架。与狂人和祥林嫂相比,阿Q即便在被枪决的一刻,也没有陷入彻底的语言幻听和形象撕裂。他的身心终结是“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巨大的创痛导致狂人和祥林嫂进入幻觉世界,但对阿Q来说,不仅任何创痛都不足以使他脱离真实世界,甚至在死亡的恐惧已经使得喝彩的人群逐渐幻化成饿狼的眼睛,他希望留在世间的遗言仍是:“救命,……”同祥林嫂对自己被阎罗大王锯裂的身体的着迷以及狂人“我已无可拯救”的暗语相比,这显示出作为阿Q言说者的那个自我具有异常强固、除了肉体的死亡,别无其他力量足以摧毁的完整性。拉康曾经在施莱伯《回忆》中指出,狂人所处的是一黄昏的世界,其中游荡着诸多灵魂以及作为其变种的尸体。就鲁迅的小说而言,这好比《狂人日记》中的被食者和《祝福》中死去家人的憧憧阴影。而祥林嫂通过承担诅咒,狂人通过被吃幻觉,都表现出与该世界达成齐同一致的热烈向往。与之相反,阿Q的世界全无阴影。一旦逃出生天,他的Q:“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儿子打老子”,“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你还不配”。如果祥林嫂在一个清醒的、略显懦怯的鲁迅笔下技巧地变成了病例化、心智全面矮化的疯狂牺牲品,那么阿Q则是仍受狂人热情侵蚀的鲁迅所创造的、一个同样被外在化,却无法全然被取消存在意义的前狂人。如果在生命终极,祥林嫂与他人包括与叙事者“我”的对话,也都可以看作她内心独白的外在戏剧化:她提问,不是要获得答案,而是要确立她与对方的不同,那么纵贯阿Q的成年生活,他与世界的语言冲突,。他与世界的不同在于他成为所有人的受害者,这在他被押赴刑场的一刻变得确切无疑。而世界之所以幻化成狼,因为他自己首先已经成为咬啮语言本我的强大力量。只是无论他如何接近疯狂,他始终不能获得祥林嫂和狂人那样崇高痛苦的清晰视野。这就是阿Q的悲喜剧。他的无阴影世界一片模糊。与狂人相比,他与世界之间不存在由于锚定危机而产生的欲望退缩和锚定错位。他与世界之间的锚定关系从未完成:他没有家庭,没有姓氏,没有职业,没有财产,没有稳定的社会群落,没有固定的欲望对象。他所有的欲望对象都已属他人,他每一个欲望对象都可以被下一个取代。这使他成为欲望链上不断滑动的抽象符号。他唯一能够重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挑动他人和社会对自己进行的责罚以及最后的刑杀,似乎只有在受到语言和肉体的咬啮般疼痛中他才能经验心理主体的持续存在。在幻想(fantasy)和幻觉(delusion)之间,阿Q的世界既无法肯定,也没有深度: “地狱?——论理,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这是Q体话语在《祝福》中顽固而知识化的总结与表述。
而一旦我们认为阿Q所谓“白盔白甲”之流是处于幻想和幻觉之间的某种东西,涓生在《伤逝》中针对女友的拒绝也就标志着从幻觉(hallucination)到幻想(fantasy)的回归,以及鲁迅小说写作生涯的终结。[17]真实世界的塌陷使得临终的祥林嫂和成年阿Q丧失了正真的对话伙伴,但狂人和涓生却享受着不完整的孤独。前者狂热呼叫拯救者,虽然拯救者保持沉默;后者在痛苦中驱离子君,虽然在他的真实生活里女友其实不存在。就像食人者之于狂人,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比较极端的读法,来指出《伤逝》中的子君并不是涓生真实的“他者”,而只是以女性面具出现的涓生本人。涓生爱子君,一如精神类疾病患者像爱他的自己一样爱他幻觉。从读者的角度看,子君的脚步声似乎是邻人脚步声的联想,她的视觉形象空洞单一,在语言上除了重复涓生表述和愿望之外别无趣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依然是涓生自己的言说,只是从子君口中传递,涓生才能知觉其字面行间的含义,从而对自己心生爱恋。阿Q不能成为现代心理叙事的主体,是由于他无法经验欲望。涓生同样不能,却是根据如下的状况:幻觉主体和幻觉角色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构成心里叙事。仍然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伊丽莎白和达西之间的内在或深度世界能够被展开,其原由无非是他们在社会动作层面无法完成的动作一度受到压抑,并转移成为内在的心理层面的动作。而只要心理动作在社会层面得到恢复,满足赤字即告消除,心里叙事即便结束。而根据拉康的看法,作为压抑的必要条件之一,恋爱中的“他者”必须在自身被恋爱主体认知的形象之外,另有主体视野无法完全触及的别样的主体存在和不可预知性。如果只有能够欺骗的神才是真神,而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偶像,相邻主体的真实性也只有在其不可预知的、对恋爱主体主观投射的否决中才能体现。换言之唯有碰壁,方生压抑。而涓生对子君的爱情畅行无阻,从不碰壁,于是无从感受压抑,当然心理叙事所依赖的内在深度、心理挫折和以自由间接引语为稳定形式的替代满足更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伤逝》绝对不是一篇常规的心理叙事,它蕴含的只是对叙事深度的无耐投射,或者说五四心理叙事只能篇幅短小的原因。而同时,心理锚定的侵犯性仍在发生作用。。但与《狂人日记》不同,《伤逝》的叙事操作引入了一个关键的话语机制,。也就是说作为涓生的替身,子君承担了涓生由于自恋而引起的自毁。正如祥林嫂之于狂人,子君的灭亡无非是涓生自毁的外在化。但造成她灭亡的直接杠杆,亦即涓生对子君的拒绝(“我已经不爱你了”),却不只造成涓生对自己的简单拒绝,而更明晰地指向他对于自己幻觉体验的的拒绝。如果涓生是鲁迅狂人的都市版和觉醒版,他得以在疯狂中脱身的至关重要的步骤就在于他用语言不是其他方式实现对子君的拒绝。他的拒绝是语言化的拒绝(verbalized rejection)。这一点对于精神类病患的康复作用无可替代,因为它保证了语言主体对自己的最后防护,使得涓生不至于像狂人一样在对拯救者的呼叫中陷入无语的疯狂。当然语言化的拒绝也让他明确认识到觉醒的丑恶和卑微。他在故事的最后希望在“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使她快意。” 病愈后的叙事者,似乎已经认识到幻觉体验的疯狂和恐怖,但是毕竟这是他生命中最为强烈的体验,所以他仍然希望拥之在怀。因为与它相比,“新的生路”,也就是狂人康复后的候补之路,显得万分空虚。但这时的拥抱已经是正常人神经质的幻想(fantasy)式的拥抱,而不是原来在精神性幻觉(delusion)中的不顾一切的爱恋和拒斥。而随着涓生的康复,随着叙事产生了愈合意义上的有效性,鲁迅由《狂人日记》开始的小说之旅也走到了尽头。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失去了疯狂母题的鲁迅当然并没有中断他的文学生涯。在小说创作之初,他就开始试验一种后来被称为杂文的文体。显而易见,其小说与杂文之间的替代关系,长期以来从未得到深切关注,似乎在虚构短篇方面的努力获得了一定成就以后,中国现代叙事的奠基人自然而然走向另一种文体的创作。然而如果着眼于《狂人日记》所标示的话语特质,我们会发现鲁迅的杂文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毋宁说是一个文体的坟场。如上所示,在他最重要的小说里贯穿着一种狂人的语言幻觉(linguistic hallucination),以及针对语言主体崩坏(亦即《狂人日记》中的语言空洞)的焦虑。其中,叙事作为对于疯狂经验的展示和解决手段使得它自身延续的唯一理由就是寻找愈合,而随着愈合路径得到肯定,不但回归疯狂不再是理性的随意选择,而且小说作为处理疯狂母题的默认或预置文体也不再成为富有活力的话语媒介。作为杂文家的鲁迅,其独特之处正式在于他成为在现代意义上自觉的、被剥夺了文体的文学家。相对于疯狂序列的超心理叙事,杂文既不构造心理深度,也不重视叙事完整。同时,也正如《呐喊》和《彷徨》中除了那些突兀而起的、简略的、纪念碑式的幻影作品外,还充斥着众多或警策、或无聊的思想和语言碎片(比如说《故乡》中的“路”和《肥皂》中的“咯吱咯吱”)一样,鲁迅杂文的基本形式,从早期的《随感录》到后来的《文人相轻》,可以说都处于某种针对文体的、后置的、前锚定状态。[18]虽然重建作者的心理构成需要更为细致和职业化的研究,但就他生平最大量的文字积累种类(即日记和杂文)两者间的关系来看,鲁迅似乎对于所谓欲望的退缩采取了过度补偿的策略。似乎他对自身的客体去锚定化倾向具有如此巨大的恐惧,所以事无巨细、日复一日、不厌重复地记载、评判他生活周遭的一切。而文体不存在,完成感不存在,正是过度补偿的前提。他的小说呈现为疯狂的诊治:在《狂人日记》以后出现的《阿Q正传》、《祝福》、和《伤逝》代表了前置(pre-positioning),旁观(externalization),和康复(recovery)三种解决模式。针对狂人的失语,阿Q从未失语;祥林嫂只是失语的他人;涓生拒斥幻觉,恢复了语言自我。或者说,在《狂人日记》文本空洞的边缘,鲁迅组织了三条步步递进、同时也相互补充的话语路径。但随着涓生的康复,这些路径都已不可持续。他的杂文则可以看做是对病症在可控状态下的享受:当文体被撕裂,当细读不再有效,原本出现在小说中的语言和思想的碎片,首先都显现为文体的碎片。在《且介亭杂文序》中他曾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19]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掩饰,因为杂文并不是以编年为结构的作品集合,而是指一种特别的作品样式。而如果把后者当成各种文学元素的纯时序排列,那么这些元素和文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也未得到说明。如果这样的言说对于理解鲁迅杂文有任何助益的话,那无非是第一,杂文中的鲁迅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逻辑,含糊其词;第二,杂文的样式的确是“各种都夹在一起。”但这所谓“各种” 并不是完篇的具有完整文体结构的文本,而是能够从属于这些结构,却又并未被组织到这些结构中间去的文体碎片。这些碎片不仅具有本身只字片纸的词典意义,而且具有特殊的作为文本碎裂形式的意义。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如果鲁迅的杂文话语在风格上与他的小说话语还存在一定继承性的话,它既不是《祝福》那种针对祥林嫂的悲悯反思,也不是涓生那种貌似悔恨、心中窃喜的幸存者陈述,而只能是阿Q式的前置话语。也许慑于作者巨大的感情纵深和话语权威,五四以来的论者鲜少在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他最著名的文学形象阿Q之间画上等号。但就从最浅表的层次看,他的杂文也正是一种在文化知识界不断找茬寻衅的Q体话语。其中说话人通过与世界的无停歇的语言冲突,。或者说杂文中各种语词、意义、和文体的碎片通过简单的时序连缀,所显示的仍然是鲁迅内心冲突的外在对白化和戏剧化,是他内在语言的迂回幻听。与《祝福》和《伤逝》摆脱疯狂的话语操作相比,《阿Q正传》只是悬搁疯狂。作为动作和动作对象之间的介质(preposition的另一个意思是介词),前置状态的重要性要超过动作及其对象本身;作为文学形象,阿Q 可以无限接近但无法最终到达疯狂这个语言极限;作为话语策略,杂文同样是一种绝对化的前疯狂言说:前置状态使得疯狂得以在语言中获得虚拟的再现,于是狂人波涛汹涌但无从表达的内在经验,亦即《狂人日记》中逼人而来的文本空洞,在杂文中通过错乱无章而鲜活生动的碎片堆积获得替代和填补。而杂文叙事者从阿Q形象的正式剥离,正是《彷徨》中反复出现的类似《祝福》中的“我”这样秉持某种前锚定语言的知识分子。狂人、祥林嫂和涓生都无法应付语言分裂(包括语言自我的形象崩塌和所谓语言幻觉,即幻听)带来的痛苦,但是以阿Q为原型的杂文作者却处处展示甚至炫耀文体失锚的好处,似乎非常享受这样作为不死的快乐原则的拟人化身份,虽然这里的所谓失锚其实是一种前锚定的状态。与此相应,设计杂文这样一种话语,无论是把它放置于疯狂发生之前,还是将它当作疯狂的替代,必然也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作者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来回应疯狂对中国现代语言的挑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话语和超话语条件造成了狂人(这个在终极意义上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纪念碑地位的形象)的极端体验。对于精神病类患者怎样陷入最后的疯狂,拉康谨慎地声称分析工作无法提供任何答案,显然后者肯定要心理正常的分析者承担进入疯狂的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拉康只是在不断恶化的病症过程的开端提出了他所谓“父名屏蔽”假说。按此假说,具有精神病潜质的人群,以施莱伯法官为例,不但不认同父亲身份所代表的权力体制及其社会制约,而且“父亲”作为语言锚定的基础(nom du père)和权力压制的来源(non du père)并未进入患者的语言自我的构建过程。所以一旦像主席法官这样具有父亲含义的职位落到施莱伯头上,后者体验的直接危机是他遭遇到了自己智力和感情资源所不够应付的巨大挑战,于是语言主体步步向最终瓦解推进,直至完全陷入疯狂。回到鲁迅,在历史和话语的交叉点,他从翻译《域外小说集》获得的创作资源同样偶然地把他放到了中国现代叙事之父的位置之上。[20]强势而一度成为死囚的祖父,和长期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父亲,这些造成“父名屏蔽”的焦虑来源再度强力冲击他具有绝世天才的语言主体,使之痛苦异常,濒临裂解,也就不足为怪。[21]
但是,在广义的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内,“父名屏蔽”如何发生,而被屏蔽的“父名”怎样具体在杂文中得到部分修复,并且为中国文化现代经验的再现提供怪异而具有感染力的话语引擎,这就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内容,必须由对文本中的幻觉换位进行近距离阅读(close reading of the hallucinatory reversals)才能加以申述。当然,即便在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鲁迅杂文与五四右翼的胡适实用主义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虽然Q体话语追求快乐,但是它最终只能是痛苦、羞辱、伤害和毁灭的承载体。而胡适以下的中国实用主义,其实也就是康复后的涓生主义,已与上述承载或表达无关。[22]从狂人的话语空洞中重新站回到陷入疯狂的边缘的现代中国文化人,不仅传统语文(文言)已经成为他人的语言,或者说严格意义上必须重新理解和获取的“陌生语”(foreign language),更重要的是,他甚至没有一种可以称为是自己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鲁迅杂文表达媒体的所谓原创性的“白话文”,不仅是一种陌生语,更是碎片化的、垃圾般的、似曾相识的陌生语。对于即将失语而永难失语的半狂人而言,白话文在被使用之前,就已经被抛弃。而我们也只有在文体和形式的坟场中,在杂乱无序的肮脏的被弃物之间,才能见证鲁迅从疯狂中奔涌而出的、显现在阿Q背后的、幻影与史诗般的存在。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木刻版画,赵延年绘
注释:
[1] 15年9月受旭东安排到重庆大学高研院访学。有次谈起他将要完成的有关鲁迅的书稿,很受触动。10月中又蒙他相招,去北大燕京学社在他的鲁迅杂文课上扮演回音板的角色,大家谈得新意迭起。于是形成了文中的大致想法。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对于本文逻辑的明确表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不愿署名的友人也贡献甚多。在重庆大学高研院,笔者曾就教于张文涛和陈颀两位同事,从他们渊博的学识中获得的不少助益。北大朱成明博士改正了我在神经质和精神病译法上的颠倒。在此一并致谢。鲁迅:《狂人日记》,见王世家、止庵:《鲁迅编年著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三卷,第19-34页。
[2] 见Jacques Lacan, Le Seminaire, Livre III, Les Psychoses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1981), p. 24.
[3] 茀罗乙德:《茀罗乙德叙传》,章士钊译(上海:尚舞艺术馆,1930)。
[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有关法兰克福学派融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论述,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有关该学派发对此种融合的论述,见哈伯马斯:《认识与兴趣》,郭言义、李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有关齐泽克汇通拉康和黑格尔的论述,见Slavoj Zizek,The Most Sublime Hysteric: Hegel with Lacan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2014)。
[6] 有关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心理分析语言在二十世纪以来去殖民化话语中的使用,见Ranjana Khahha, Dark Continents: Psychoanalysis and Coloni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802页。
[8] Sigmund Freud, “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in The Freud Reader, edited by Peter Ga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9), 301-308.
[9] 鲁迅:《阿Q正传》,《鲁迅编年著译全集》,第四卷,第330-362页。
[10] 有关主体的语言只能由被外化的他者来言说,见Lacan, Livre III, p. 63.
[11]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2] Dorit Cohn,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14)。
[14] Daniel Paul S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Translated by Ida Macalpine and Richard A. Hunter. 1955.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 拉康1955到56年间在圣安娜医院的讲座就是以施莱伯《回忆》为蓝本对精神类病成因和状态的系统探讨。见Jacques Lacan, Livre III. 关于他晚期对精神病理论的补充和改订,见Le Seminaire, XXIII, Le Sinthome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2005).
[16] 鲁迅:《祝福》,《鲁迅编年著译全集》,第五卷,第156-169页。鲁迅:《呐喊》,见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一卷,第437-598页;《彷徨》,见第二卷,第5-162页。
[17] 鲁迅;《伤逝》,《鲁迅编年著译全集》,第六卷,第381-398页。
[18] 鲁迅:《故乡》,《鲁迅编年著译全集》,第四卷,第10-25页;《肥皂》,第五卷,第184-193页;《随感录》,第三卷,第71-73页,第76-80页,第86-88页;《文人相轻》,第十八卷,第259-260页。
[19]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鲁迅编年著译全集》,第十九卷,第509-510页。
[20] 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书社,1921)。
[21] 关于鲁迅祖父,见曹振华:《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一期,第140-143页。关于父亲和身份认同, 见张向东:《“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从鲁迅小说中“孩子”命运看其对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思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十五卷第四期,第563-568页。
[22] 有关鲁迅与胡适的文体差别,始于陈颀先生提的问题,在此只能作为文章的结尾简单交代一下,待以后有机会详论鲁迅杂文时再作阐明。
欢迎投稿,来稿请寄:Pourmarx@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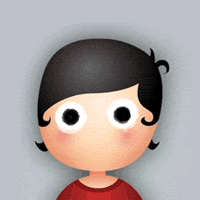
Copyright © 重庆钢铁护栏交流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