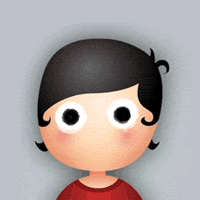天色如墨,暴雨滂沱,浓墨般的乌云将夜空遮蔽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亮也没有。
“这鬼天气!”
听得风把门窗吹得啪啪作响,一直习惯于女扮男装的的楚轻从房里走出来,却被带着雨丝的冷风吹得狠狠打了个哆嗦,忍不住骂了一句。
来古代七年了,她还没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每到这种下雨天,她就会无比随闷!
只可惜,今非昔比。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院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且又杂乱的声响。
楚轻条件反射般地竖起了耳朵,自语道:“这大雨天的,不会又出事了吧?”
“楚轻,楚轻!你在家吗?”
是小满的声音!
小满是住在她家隔壁的一十六七岁小男生,从楚轻穿越而来后,每天除了师傅外便是小满不断的在她耳边叨哔。
外面的敲门声还在持续,而且有越敲越重的趋势,再这么敲下去,楚轻觉得那个年久失修的破院门肯定就要以身殉职了。
“来了!”她随手拿起窗下的油纸伞撑开,快步走了过去。
院子外头,楚轻的青梅竹马加邻居小满同学正趴在院门上的缝隙往院子里张望着,待看到楚轻出来,顿时提高了声音。
“大爷们,看吧,我都说屋子里有人嘛。”小满扭过头去望着身那几个人,白净的脸上露出几分得意地道。
“什么事啊?”楚轻开了门,顺便查看了门板,确定它还没碎,这才放下心。招头望向小满,这才发现小满还带了不少人来。
“好事,大好事!”小满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边来,在她耳旁嘀咕道,“赵府的梅姨娘死了!”
看到小满喜气洋洋的表情,楚轻不禁满头黑线。
“梅姨娘?”她在脑海里快速过了一遍这个名字,确定这个人跟她和小满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更加满头雾水了,“她死了,你高兴个什么劲儿?”
难不成小满和那个什么姨娘有仇?
“你傻呀?”小满恨铁不成钢地望着她,那,“现在是赵府的管事亲自来请你去殓尸呢!你不还想修揖房子吗?这赵府给的赏金必定不少。”
“叫我去……殓尸!?”
楚轻一愣,下意识地转身望向小满带来的那些人。
而看到楚轻的正脸,外头几个人不由得一愣。
大雨中,执伞的小哥儿身姿纤秀,鸦鬓雪肌,一袭最寻常的青衣穿在他身上,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令人眼前一亮。
世上竟有男子生如如此俊秀!
可是这小哥儿说话的口吻,跟他清秀的外表却实在是格格不入。
“那个……”为首的男子最先回过神来,立刻说道,“我们府上出了事,想请你们去验看一下尸首。”
说话间,楚轻已经看清了他们的衣饰。
他们的衣裳布料倒是不错,却是大户人家下人的款式。
这大下雨天的,楚轻本来就不想出门,一见不是官府中人,就更没了耐心。
“我家师傅外出几日,县衙的案子还压着没去看呢,抱歉让几位白跑一趟了。”白了一眼小满,楚轻礼貌地拒绝了他们,说着就要关上院门。
贵人后院的事情,且又是这种绕过县衙直接来找他们的私活儿,怎么也不能接。
谁知那领头的管家却十分机敏,见她要关门,竟然眼疾手快地伸了胳膊进来,硬是将门撑开一条缝。
“张师傅不在,那劳请楚小哥走一趟吧!”
楚轻关门的力道不小,那管家的胳膊夹在门缝里,疼得声音都变了调。
瞅着门缝里那条被夹得直抽抽的胳膊,楚轻却没什么怜悯之心,反而加大了手上的力道,将门板再次推紧了些。
“死者是女子?”她的声音丝毫没有祸害人的内疚,而是带着几分冷静。
“是……是……”管家几乎是从牙缝里迸出这几个字,无奈有求于人,连求饶都不敢。
“既是女子,自有稳婆验看,为何来找我?”
按照正常的流程,若是有女子尸首需要验看,不便之处都是找稳婆代劳,怎么会找到她头上来?
管家的胳膊被越夹越紧,此刻已经疼得死去活来,一个大男人,声音都带了哭腔:“这事……实在因为内有隐情,我们老爷发了话,请您还是走一趟吧!”
楚轻冷笑,大户人家能有什么隐情,无非都是些龌蹉肮脏的事,她可不想蹚这种浑水,她又不是来古代学做好事的。
眼看着她不出声应允,管家心急如焚,冲身后的小厮怒道:“你们几个是死人啊?还不赶紧求求楚小哥?”
几个小厮面面相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
“楚小哥,您就行行好吧!”
“我们几个一辈子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说话的声音参差不齐,生硬干涩,一听就是没排练过的。
想想也是,他们这种在大户人家的世仆,跟着主人家也有些脸面,何曾对出身贱籍的人开口相求过?
带头的管家倒是能屈能伸,竟然顾不得胳膊还被夹在门里,一下子跪倒在门口的泥水里。
“事关我们府里上下一干人等的性命,还请楚小哥无论如何也要走一趟!”
破旧不堪的门板松了松,管家还当楚轻改变了主意,顿时大喜过望。
他站起身,揉着获得解放的胳膊上前几步,正要说些好话,却见门砰地一下重新合拢,差点儿撞上他堆满笑容的脸。
“验尸要县衙出具的验状,拿到了再来吧!”
管家愣愣地盯着几乎贴在他鼻尖上的门板,一时竟没回过神来。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这姑娘难不成真是铁石心肠?
常年跟死人打交道的人,果然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
听到楚轻离去的脚步声,管家急了,顾不得怕人听见,忙高声道:“我们赵老爷和县令大人是至交好友,定不会为难楚小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却见小满露出一张喜悦的笑脸,一把拉了楚轻就往外走:“别愣着了,快走吧!这可是个肥差,若是做好了,赏钱肯定少不了你的,比你平日里辛辛苦苦上山采药强多了!”
楚轻怔怔地被小满半拖着走,一边听着小满喋喋不休的唠叨。
虽则她前世是资深的法医专家,来这里以后也跟着师傅做一些殓尸验尸的事情,想来赵府的这件事情也难不倒她,但像赵府这种高门大家后院之事,她内心必然是不想参与其中的。
只是在小满的半拖半拉之下,很快,就到了赵府的后门。
除了在电视上看过,楚轻还是第一次亲身走进这种大宅门。
过了大门是二门,过了二门进内院,楚轻走的头晕脑胀,深恨当年没有选修古代建筑结构这门课。刚过了二门,小满便被大院里的下人给拦住了。
与小满交流了下眼神,楚轻便被管事交给了后院的李婆子。
赵府的宅院在古桥村是数一数二的大宅子,即使是勘验过无数现场的楚轻,也不禁有些惊讶。
小桥流水,白石栏杆,精致的亭阁,嶙峋的奇石,要不是楚轻在古水村生活了七年,她还以为自己正身处京城里的大户人家。
沿着鹅卵石铺就的甬路走出后花园,绕过几处院落,李婆子在一处不大不小的院子前停下了脚步。
“……人就在西厢房,你自己进去吧。”说完,李婆子像是躲避什么似的,快步离开了。
前脚才迈进院门,她就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
下着大雨的院子里齐刷刷跪着数十个人,要不是楚轻早已习惯了自己穿越的事实,她还当又不小心进了西安的兵马俑坑呢。
楚轻瞅了一眼管事妈妈,对方双眉紧蹙,轻轻摇了摇头。
这哑语打的是什么意思,楚轻有些不解。
楚轻皱了皱眉,心里涌上一种不好的预感。
红漆的院门虚掩着,她试探地推开门,还没等看见院子里的情形,就听见一声霹雳般的怒吼。
还没等她开口,就听见上房传来一阵哗啦啦的脆响,仿佛是什么东西被摔碎了。
“你给老子闭嘴!”一个男人雄浑的咆哮声传了出来,即使隔着滂沱的雨声,那声音依然很震耳,“梅娘的死因老子一定要查清楚,就算是毁了尸首也在所不惜!谁再敢劝,老子就把她当凶手,拖出去打死!”
回应他的,是一阵呜呜咽咽的女人哭声。
管事妈妈带楚轻来到门外,轻声说道:“启禀老爷,忤作到了。”
“给老子进来!”浑厚的男人声音响起,带着明显的余怒未消。
楚轻拍了拍衣角的雨滴,挺了挺没啥料的胸,迈过了门槛。
正屋里的情形跟外面查不到,同样是跪了一地的人,只是这里头跪着的女子们明显比外面的档次高一点,一溜儿的莺莺燕燕,花红柳绿的倒是好看。
楚轻踩过一路的绫罗绸缎,目不斜视地走到这屋里唯一的男人面前。
或许是武官出身的原因,赵老爷的身材很是魁梧,若不是鬓角的白发和脸上的风霜皱纹,倒看不出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
从楚轻一进屋,赵老爷的眼神就一直盯着她,待她走近,看清她那张年轻得过分的小脸,赵老爷的脸色更黑了。
“你就是跛子张的徒弟?”
“是。”楚轻不卑不亢地说道。
质疑的目光她见得多了,前世就经历过不少,如今更是见惯不怪。
赵老爷的目光如鹰隼,锐利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就在楚轻以为他要出言考验自己的时候,却听见他开了口。
“人停在西厢房,你给老子验准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赵老爷刚硬的脸上带了几分掩不住的虚弱但却仍掩不住他威胁的意味。
看得出来,死者定是个他十分在乎的人。
楚轻一言不发,没有再看那几个满身鲜血的女子一眼,径直进了厢房。
不该看的别看,不该管的别管,不该问的别问,这是她两世为人的处事准则。
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银子,这是楚轻两世为人始终都信奉的座右铭。有说废话的功夫,还不如多看几眼尸首。
推开西厢的房门,一股带着雨丝的风吹了进去,房间里的烛火顿时摇曳不定,变得忽明忽暗起来,透出几分阴森森的气息。
楚轻推开厢房的门,看清床上的尸体,脸色顿时变了。
女尸的腹部高高隆起,明显与身体其他部位不成比例,如今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尸体看起来又是新死不久,绝不可能是腐败之气聚集在腹部导致的。
片刻之后,她就有了结论。
“她怀孕了!?”
不敢看楚轻陡然犀利的目光,更不敢看房内那死相恐怖的尸首,站在门外的管事妈妈别过了脸。
“是……已经快足月了。”
一尸两命,楚轻此刻终于理解了赵老爷的愤怒。
顾不得多想,她一把拉开房门,冲院子里高声说道:“我需要一把刀,还要剪子,快!”
刀?剪子?
院子里的众人愣住了。
殓尸不就是擦洗尸体,整容穿戴之类的吗?要刀剪干什么?
赵老爷最先回过神来,原本难看的脸色立时沉了下来,厉声道:“你要干什么?”
楚轻抿紧嘴唇,一字一顿地说道:“剖、尸。”
听到这两个字,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赵老爷更是怒容满面。
“不知好歹的小贱种!”积蓄许久的怒火,终于被楚轻这个惊世骇俗的要求彻底点燃,赵老爷扬起手中的鞭子,唰地朝楚轻抽了过来。
眼看着那带着浓重血腥味的鞭子就要落在自己身上,楚轻脚步轻移,身形灵巧地避开了那雷霆般的一击。
看着暴怒的赵老爷,楚轻俏脸含霜,冷声道:“你还想不想要孩子!?”
这句话就像是一句符咒,让已经扬起第二鞭的赵老爷硬生生收回了手。
“你……你说什么?”他满脸的震惊,不敢置信地看着楚轻。
楚轻不愿再多废话,只是重复了一遍她的要求:“我需要刀和剪子,要快。”
赵老爷死死盯着她的脸,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可以信任的东西,又似乎在做着什么艰难的抉择,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去拿给她!”
顾不得多问,快速检查了一番,楚轻猛然回头,冲门外说道:“快去准备热水!”
“热水?”管事妈妈一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验尸吗,要热水干什么?
可是看楚轻又回头去摆弄尸体了,管事妈妈不敢再问,赶紧转身去了。
西厢房内,楚轻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柄造型奇特的锋利小刀,沿着尸首肚脐与耻骨联合之间的正中线,稳稳地切了下去。
剖腹产竖切,是取出婴儿最快的方式。
皮下脂肪、肌膜、腹肌、腹膜层、子宫肌肉层,最后是羊水腔,每向下划开一层,楚轻的手都越发稳健小心,因为此时此刻,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划伤婴儿。
管事妈妈取了热水才刚进院,就听见西厢房传出一声极微弱的婴儿哭声。
渐渐变小的雨声中,婴儿的哭声一声比一声嘹亮,那些原本跪在院子里如泥塑木偶般的下人,此刻齐刷刷地盯着哭声传来的厢房,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震惊和错愕。
赵老爷大步走了出来,走到门口却有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房门,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所有人错愕震惊的目光中,她神色平淡地看向张着嘴一脸不可思议的管事妈妈。
而楚轻却像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旁人紧张的心情,全副注意力都放在手中正在做的事情上。
似乎过了许久,一个小小的,周身沾满淤血的婴儿,终于从女尸的腹部取了出来。
众人紧紧盯着楚轻手中的婴儿,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院子里静得落针可闻。
如果费尽周折取出来的却是个死胎,老爷肯定饶不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子!
这时,只见楚轻握住婴孩的脚腕,将婴儿倒提起来,抬手就朝孩子的后背重重拍了几下。
“把孩子好好洗洗,免得过了尸气。”
房间内外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楚轻的动作。
赵老爷顿时变了脸色。
眼看孩子已没了气息,怎么还要如此重手地拍打婴儿?这女子难不成是个疯子吗?
他刚要开口怒骂,却见那浑身青紫的婴儿动了动,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婴儿脸色青紫,小嘴却大大地张着,一边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一边发出阵阵的哭声,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来到这世界的方式是何等的惊悚。
洪亮的哭声打破了院子里那死一般的静谧,所有人的神色都为之一松,更有几个仆妇喜极而泣。
“活了!竟然真的活了!”
“还是个小少爷呢!”
“呜呜,梅姨娘在天有灵,佑护小少爷平安降生啊!”
众人中神情最激动的,自然是赵老爷,但此激动却并没有半分当父亲的喜悦,反倒像是……带着绝处逢生的激动。
他微微颤抖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一个周身戾气的大男人,此刻眼中竟然带着点点的水光。
楚轻找了块干净的布,将孩子包裹起来,递给赵老爷。
“给孩子洗干净,免得过了尸气。”
赵老爷低下头,看着襁褓中哇哇啼哭的婴儿,神情激动又喜悦。
“是男孩儿!老天自不亡我!”赵老爷说了句让人费解的话。
他贪婪地盯着婴儿小小的脸庞,好一会儿才不舍地将孩子递给一旁的管事妈妈:“听见楚小哥儿的话了吧?去给孩子好好洗洗。”
楚轻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到尸体身边。
从小贱种到楚小哥,这转变也真够快的,不过她没心情跟赵老爷计较,孩子取出来了,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赵老爷望着她忙碌的背影,欲言又止。
过了好一会儿,他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沉声问道:“楚小哥,你能否验出梅姨娘是中了什么毒?”
“中毒?”楚轻收拾的动作顿了顿,下意识地看向还没完全整理好的尸首,“你怎么知道她是中毒而死?”
赵老爷仿佛有些难以启齿,半晌才低声说道:“老夫正室早亡,几个小妾一直不睦,自从梅姨娘怀孕后接连出过几次事,不是偷偷下巴豆就是暗地里给饮食里加红花的,所幸没闹出什么大事来,谁知这次……”
话一开了头,后面就好说了。
赵老爷沉重地叹了口气:“这次若不是楚小哥出手,这个孩子怕是就跟梅娘去了。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这事若是不查个清楚,老夫心中实在难安,还望楚小哥帮这个忙。”
像赵老爷这样的人,能这样纡尊降贵地跟楚轻这种出身贱籍的女子说话,已是给了天大的体面了。
可是他说了这么半天,楚轻却恍若未闻,始终背对着他,默默地整理着尸体。
赵老爷等了好半天,楚轻才头也不回地扔过来一句话。
“她不是中毒死的。”
“什么?!”这个结论对赵老爷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张目结舌地望着楚轻的背影,下意识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楚轻举着沾满血迹的双手,转过身,面无表情地直视赵老爷。
“死者口鼻间、消化系统干净无出血点,肌肤、牙齿、头发色泽均未见异常,周身不见任何中毒迹象。”她语气平板地说完了自己的结论,冷漠地扫了赵老爷一眼,“你从哪儿看出来她是中毒死的,屈打成招吗?”
此话直指院子里那一幕,竟然将赵老爷噎得一怔,想说什么却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而楚轻却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反应,而是转过身,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了。
房间中静默了片刻,窗外传来几声女子微弱的呻吟,赵老爷顿了顿,才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般地,沉声问道:“烦请楚小哥查明梅娘的死因,老夫不胜感激!”
“可以。”楚轻手中动作未停,声音一如刚才地冷漠,“就怕你舍不得。”
赵老爷起初不明白这话的含义,但是很快,他就知道楚轻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斧子,锯子,凿子……听着楚轻接连报出需要的工具,赵老爷的脸色越来越白。
刚刚亲眼看着楚轻剖腹取子的场面,此刻他完全不敢再看房里的情形。他转身下了台阶,站在院子里,耳听得西厢房里时不时传出来的凿锯声,完全不敢想象房间里的情形。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楚轻终于走了出来。
赵老爷循声望去,那几个吊在树上的女子更是抬起头来,乞盼哀怜地望着楚轻,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楚轻只看着赵老爷,神情淡漠如水。
“死者,女,身长五尺二寸,年约二十二到二十五岁,已有身孕九个月,死亡时间昨夜亥中至丑初之间。身着白绸竹叶立领中衣,头戴翡翠兰花簪一支。身体丰纤合度,肌肤白皙,左臂中关穴外侧有豆粒大小红痣一枚。头发浓密光泽,牙齿齐全,周身无明显外伤,口鼻间未见异状,肠胃、血液均未发现中毒迹象,未发现内脏器质性病变,排除窒息、中毒及病死的可能……”
一连串的专业术语,让房里的人都听得有些一头雾水,但是最后一句话,大家倒是听明白了。
几个跪在地上的侍妾顿时松了口气,一个身着粉绿色衣衫的女子带头哭了起来:“老爷,您听见了吗?真的不是我们下的毒……”
赵老爷似乎没听见她们委屈的哭声,他猩红的眼睛紧紧盯着窗边炕上那个小小的襁褓,脸色由青转白,又由白转青,半晌才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沉声问道:“那她是怎么死的?”
楚轻顿了顿,继续说道:“死者心脏上布满红玫瑰色的血斑,心肌纤维有撕裂伤,心室内外均有大量出血迹象,这是她死亡的真正原因。”
心肌撕裂?大量出血?
赵老爷缓缓转向楚轻,目光中带着掩不住的震惊:“你是说,有人打的她受了内伤?”
到底是做过官的人,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猜测仍然与事实大相径庭。
好在这种情况楚轻早已习惯了,她耐着性子,尽可能详细地解释道:“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肾上腺会突然释放出大量的儿茶酚胺,促使心跳突然加快,血压升高,心肌代谢的耗氧量急剧增加。过快的血液循环如洪水一般冲击心脏,使心肌纤维撕裂,心脏出血,导致心跳骤停,致人死亡。”
看着一屋子满脸都是鸭子听雷表情的众人,楚轻深吸了一口气。
“简而言之,她是受惊吓而死的。”
惊吓!是什么样的惊吓,竟然会把一个人活活吓死?!
得到这个结论,赵老爷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目光中渐渐凝聚出熊熊的怒火。
“梅娘怎么会被吓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暴怒的赵老爷,所有的人顿时噤若寒蝉。而在赵老爷怒视的目光笼罩下的楚轻,却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将手中那块沾满血的布丢在地上,她淡淡地说道:“我只负责殓尸,要查出凶手,你应该去寻捕快。”
直到正午时分,楚轻才走出了赵府。
小满在外面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见她出来顿时眼前一亮,刚要朝她扑过来,看清她满身的血迹立马硬生生停下脚步。
“都弄完了?”虽然不敢靠近,却不耽误她连珠炮般地提问,“府里的人没难为你吧?你忙了半天累不累?对了对了,赵老爷给了你多少赏钱?”
看着他雀跃不已的样子,楚轻皱了皱眉,停下了脚步:“小满,下回像这种事情你可记住别把我拉下水了。”
楚轻想起赵老爷心里还打了个颤。想想刚才赵老爷讲的梅姨娘经常被院里小妾毒害时,表情及语气都很反常,总让人感觉到梅姨娘并非他的女人般。
“嘿,楚轻,做人可不能这样子!”小满看了看四周又压低了声音,满脸期待地望着她,“赵府可是大户人家,像这种活,就算没有一两银子,也有八百个钱,以你和张师傅在县衙里当两年差也赚不了那么多钱。”
看到小满那副财迷兮兮的样子,楚轻斜斜地乜了他一眼,从袖袋里拿出一包沉沉的东西往小满怀里一塞,小满急切地打开小包。
“五、五十两银子!?”小满的眼睛顿时瞪得老大,脚下一个趔跄,差点儿摔倒,冷静了好一会,才一脸的不可置信地叫道,“太好啦,我就知道这是个肥差!”
他高兴地忘乎所以,竟然一把拉住了楚轻的手:“有了这五十两银子,发达了,根本不需要修揖房子,直接在镇子里都能买到一个房子了!”
像他们这种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哪里见过这么大一笔钱?
验出了梅姨娘的真正死因,赵老爷拿出五十两银子赏她,楚轻怎么都觉得这是赵老爷给她的封口费。
看到小满激动的样子,楚轻的心却是沉沉的,内心总有一股不详的预感。
“这么多的银子,你……你想好要怎么花了吗?”
“没想好。”楚轻越过小满道,“这些钱你爱拿拿去!”
*
这日便是师傅回来的日子,一大早,楚轻就早早起来,把院子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顺便把鸡窝里的几枚蛋捡了出来,放到厨房的灶台上准备留作晚饭。
平日里这些鸡蛋都是留着换钱的,师傅一个也舍不得吃,就算偶尔留下几个,也都让给了楚轻吃。
眼看着日头西落,楚莲却始终没回来。
楚轻在院门口翘首盼了好久,直到绚丽的晚霞布满了天空,才看见村头路口那边出现一个人影。
她心头一喜,待看清那人的身形却又不免有些失落,那人头戴青帽,身材瘦长,明显是个年轻男子。
那人在村头停下脚步,跟正在收茶水摊子的田婆子说了几句话,楚轻只看见田婆子向她家的方向指了指,那人便朝她走了过来。
天色已暗,待那人走近,楚轻才看清那是个青衣小厮,看起来十八九岁的模样。
这小厮径直走到楚轻面前,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冷冰冰地说道:“你就是跛子张的徒弟?”
听到这句话,楚轻的心头不知为什么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
她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很明显,这个人是来找她的。
“是。”她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忍不住追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师傅呢?”
小厮的话宛如一道霹雳,瞬间炸响在楚轻的耳边。
“你师傅客死龙门镇,你赶紧跟我去收尸吧。”
客死?收尸?
楚轻只觉得眼前一黑,暮色笼罩的大地仿佛一下子翻转了过来,她需要紧紧攥住门框,才能够支撑自己不倒下去。
“你、你说什么?”她无法重复那个字,只是从牙缝里艰难地迸出这句话。
她多么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噩梦,可是即使她的指甲深深嵌入了朽坏的木框,痛得心头发紧,青衣小厮那不耐烦的嘴脸却还是不肯从她的面前消失,口中说出的每个刻薄的字都像是一把利剑,毫不留情地刺穿她的身体。
“跛子张死了!”小厮抬眼看了看天色,越发地没了耐心,“别磨蹭了,天都黑了,赶紧跟我走!”
夕阳最后一点余光从天边沉了下去,整个古桥村笼罩在阴沉沉的夜色中,不知哪里吹来一阵清冷冷的夜风,吹得楚轻浑身冰凉。
再开口,仿佛连声音都不再是自己的了。
“怎么可能?我师傅好端端的怎么会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暗中陡然响起少女的声音,因为骤闻噩耗而微微有些变调,小厮不禁吓了一跳。
待他回过神来,不耐的语气中已带上了浓浓的鄙夷。
“你叫唤什么?跛子张去贵人家验尸,一时贪财偷了贵人家的东西畏罪逃跑,结果掉进井里,若不是贵人宽宏大量,不予追究,连你的小命也保不住!你还有脸在这儿叫?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师傅是个贼?”
小厮的声音一声儿比一声儿高,句句理直气壮,仿佛这样就能压过楚轻的质问。
此时的楚轻无暇顾及邻居会不会听到,只是被小厮的话气得悲愤交加,一股热气直往上涌。
师傅偷了东西?这怎么可能!
没错,他们是出身贱籍,是穷苦人家是贱民,可是师傅一直教她做人要清清白白,即使是穷也要有骨气,他怎么可能会去偷东西!?
“不可能!你们是污蔑!我要去——”楚轻刚说到这里,陡然想起了什么,瞬间咬紧了牙。
师傅这次是受邻县县衙召去协助破案的,难道她还能去县衙喊冤吗?就凭她一个小小的贱民,怎么可能斗得过一县的父母官?
原以为自己早已适应古代生活的楚轻,七年来第一次如此痛恨这个不平等的封建制度。
看到她咬紧嘴唇微微颤抖的模样,小厮面露不屑:“怎么着?你还想找茬生事?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是不配!?”
夜间村落安静,这边的动静早已吸引来不少围观的村民,眼见得人越聚越多,小厮的声音越发的嚣张:“告诉你,跛子张是人赃俱获,临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偷来的东西呢!这等偷鸡摸狗的贱民,自尽都是便宜了她!”
楚轻仿佛没有听到小厮那些羞辱的话,只是泥塑木雕般立在院门口,整个脑海里都回荡着小厮的话,如雷鸣般轰响。
师傅死了……
她再也看不到师傅慈爱的笑脸,再也听不到师傅做好饭菜低声地唤她吃饭,又劝她多吃的声音了。
在这个冰冷的古代社会,她再也没有任何亲人,只剩下孤单一人了。
小厮骂了半天,才在村长等人的劝说下悻悻地离去,临走前扔下一句话。
“明儿若不去收尸,就把尸首丢去乱葬岗喂狗!”
*
这日清晨便起了薄雾,柳梢含绿,春雨濛濛,空气中弥漫着化不开的湿气,万物似乎都被这雾雨压得喘不过气来,天地间一丝声音也没有。
路尽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沉重而缓慢。
浓雾中出现一个纤细的身影,粗衣布鞋上沾了许多泥点,粗粝的麻绳深深勒在她的肩膀上,她却依然倔强地笔直向前。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拉得动身后的木车。
车上铺着几张破烂的草席,草席下,一具尸首的轮廓依稀可见。
古桥村就在眼前,楚轻脚步稍顿,肩上的麻绳微松,她才发现肩膀处已经是钻心地痛。
她重新调整了麻绳的位置,咬紧牙关,继续前行。
师傅,徒弟带你回家了。
卖水的田大娘刚搬了火炉出来,就看见了这一幕。
眼见得楚轻肩膀处血迹斑斑,却依旧一步一滑艰难地向前,田大娘扯出一条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水光。
天地间,那个羸弱的身形步伐艰难,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家的方向挨着,虽然极慢,却是越来越近了。
在楚轻的身后,田大娘略带哽咽的唏嘘飘散在风中。
“可怜老张啊……贵人的银子,哪是那么好赚的哟!”
村中一个稍显齐整的院子里,小满娘正死死拉着小满,不让自己的儿子冲出门去。
“娘,你放开我!我要去看楚轻!”小满拼命挣脱着,小脸满是倔强,冲着院外嚷道,“楚轻,楚轻你等等我——”
“我的小祖宗,你就别闹腾了!”小满娘急得要命,赶紧捂住了儿子的嘴,惊慌失措地向外张望着,一脸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娘知道你跟楚轻关系好,可是你别忘了,她们得罪的可是县衙里的贵人!你没瞧见么,连村长都不敢出头,咱们家就更不能出去了!”
看着被捂住嘴的小满呜呜直叫,脸上表情急切悲痛,小满娘也不禁落了泪。
“娘也知道,楚轻是个好孩子,可是这娃命不好,被跛子张收养注定是个贱民……”小满娘扯起衣襟擦了擦眼泪,哽咽道,“这个时候,咱们家真不能沾楚小娃的边儿啊!就算你不怕,你也要为你爹想想啊,你爹好不容易才得了教馆的差事,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给他添乱哪!”
听到娘的话,小满知道,今天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去了。
耳听得楚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小满扑通坐在地上,心疼着楚轻。
小满娘稍稍松了口气,见儿子这副模样十分心疼,不禁放缓了语气:“小满,要不等到了晚间,你偷偷去瞧瞧,也算是尽了心意了。”
小满哽咽难言,只是点了点头。
行走在村子里的楚轻仿佛没有听到外界的任何声音,只是机械般地向前走着。
往日的这个时候,村子里早就是热闹喧嚣的场景了,开门扫院子的,喂鸡喂猪的,扛着锄头下地的,打水的洗衣服的,构成一副楚轻再熟悉不过的村落生活图。
而今天,此时此刻,村子里却是一片死寂,家家院门紧闭,悄无声息,似乎生怕一开门就沾染了什么晦气似的。
楚轻低着头,全身的力气都放在拉车上,脊背却始终保持着挺直。
师傅必定是不会是偷了东西畏罪自尽的,即使全世界都不相信师傅,她也坚信这一点。
可是要为一个出身贱籍的忤作洗刷冤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更何况,给师傅定罪的人是一县之主。
她只能靠自己。
两世为人,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感受到这样沉重的压力。
将师傅的尸体背入院子,放在她离开时设好的简陋灵床上,楚轻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师傅,你信我,我一定会还你清白!”
她不信什么在天之灵,不信什么神仙保佑,她只信自己。
洗净手脸,换了件干净衣服,她走到了灵床前。
深吸了几口气,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缓缓掀开了草席。
尽管她之前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客观,只当自己在检验一具普通的尸体,只当自己是在工作,可是在亲眼看见师傅的尸首的这一刻,她依然无法完全克制自己的情感。
熟悉至极的脸庞近在咫尺,依然是那样的慈祥,却再也没了任何的生气。灵床上的师傅双目圆睁,牙关紧咬,尸首呈僵直状,典型的死不瞑目。
而深谙法医学的楚轻却知道,所谓的死不瞑目,只是在人死亡的那一刻,眼轮匝肌没有接收到大脑传出来的闭眼信号,所以才会没有闭眼而已。事实上科学已经统计过,在死亡的时候没有闭眼的死者大约会占到四成以上,因此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她强行控制住微微发抖的手,解开了跛子张的上衣,开始进行全身检查。
在看清衣服下露出的大片青灰色肌肤时,楚轻的脸色顿时变了。
她咬紧嘴唇,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继续默不作声地验尸。
这是她两世为人以来,第一次检验自己亲人的尸体。
过了许久,她才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块白布盖住了尸首,动作轻柔而细心。
做好了这些,她走到一旁,拿出了纸笔。
整个过程只有她一个人,记录的也只有她一个人。
“死者楚庭张,人称跛子张,男,年龄四十六岁,死亡时间为两日前丑时前后,额部有一处直径为一寸三分撞击伤,导致颅骨凹陷,伤口周围呈打伤色。左脸颊,左前臂外侧,双腿外侧有擦痕,皆为打伤色。”
所谓的打伤色,是法医勘验中的一种说法,是指血液呈暗黑色的伤口,这种伤口是指血液凝结之后,也就是血液循环停止之后打出来的颜色。
按照县衙给的说法,楚庭张的尸首是在后院一处荒废的井里发现的,里面的水早已干涸,楚庭张跳井自尽,是头部撞上了井底的石块而死。
按照额头处的撞伤和身上的擦痕伤来看,楚庭张的确是掉进了井里,但是这些伤口,却是在楚庭张死去以后才形成的。
也就是说,楚庭张在被扔进井里之前就已经死了。
楚庭张克制住心中的悲愤,继续记录着。
“尸体颈部,腰腹,四肢处,共有瘀伤二十七处,大小肿块六处,刀伤十四处,双手指尖多处馈烂,疑为刑具所致、,不计其数……”
越往下写,她的手颤抖得越厉害。
与之前的那些伤口不同,这些伤口都是有生活反应的,她无法想象,在师傅死之前,曾经遭受过何等残酷的折磨。
楚轻深吸了口气,在尸检单的最后处写下了结论。
“死亡原因:虐杀。”
随着“杀”字的最后一点落下,一阵带着寒湿之气的冷风骤然吹起,吹得灵床上的白布微微飘起,小小的院落里竟多了几分阴森森的气息。
楚轻顺着风吹过的方向望去,看着白布下楚莲一动不动的尸体,目光渐渐冷然。
“师傅,我楚轻对天发誓,一定要找出杀你的凶手!”细雨中,少女神色刚毅,声音如寒冰般冷冽,“即便他是皇子王孙,我也一定要他为你偿命!”
楚轻狠狠抹了一把脸,再站起身时,肃穆的脸上孤傲清冷,眉宇间的坚贞,在身后绵绵的细雨中如同青竹般坚韧不屈。
她走到角落里,把从龙门镇带回来的师傅的仵作箱带到了灵堂前。
上面沾了血渍与泥水,楚轻一点点擦拭干净了。
打开了仵作箱,里面摆放整齐的三层,此时却是凌乱的。
师傅用以糊口的这个仵作箱,若非当时情况紧急,他怎么可能丢下自己的仵作箱而一人死在离刘家那么远的枯井里?她想要替师傅报仇,那么在此之前就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查出师傅无故惨死的原因,他死前遭到虐待,更像是刑讯逼供,对方逼问的是何事?
刘家请师傅去龙门镇去验尸,过的是成县令的手,她第一个要去质问的,就是成县令!
而第二件则是写状纸喊冤,让成县令立案彻查师傅死亡的真相。
可是以成县令畏权怕势的性子,怕是不会得罪龙门镇的那个贵人——刘家。京城刘家的一个旁支,因为当朝刘国舅与刘太后的缘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龙门镇作威作福,相连的几个镇鲜少有人敢得罪他刘家的。所以想要让县令大人立案,就必须有一个由头,一个能前往龙门镇刘家的由头。
最后一件事却是跟她有关。
所有人都知道师傅得罪了贵人,怕是没人敢替他验尸,那么既然她是师傅唯一的徒弟,那么这个衣钵也就由她继承下去,由她来亲自让他老人家的尸体向众人开口喊冤。
楚轻在楚庭张的灵堂前守了三天三夜,然后才下葬,等她做完这一切,已经是第四天的清晨了。
她从林间回来,踩着一地的晨露,一袭素色长袍,白色的绸缎束发,衬得身姿纤细挺拔,像极了一根青竹,看似单薄无依,却刚毅挺拔。
她怀里放着一纸状书,到了衙门前她就击鼓鸣冤,若是成县令不肯接,那么她就必定想尽办法进衙门里,不管用什么代价,都要让成县令给她一个交代。
楚轻途径清水镇的清水河时,前方却是围了不少的人,吵吵嚷嚷的,好不热闹。
天刚擦亮,楚轻经过时,听了一通,大概是河里溺死了一个人,苦主的婆娘抓着一个疑凶不放手,以至于闹得衙役来了不少,妇人的哭嚎声嚎得楚轻不由多望了几眼。然她怀里还有一份状纸,她并没忘记她此行是给师傅报仇的。
“……天杀的啊,你怎么就能这么狠下心啊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啊,干脆我也死了下去陪你算了,苍天啊为什么死得不是我啊!”哭嚎声拔高了尖响彻在凉风送爽的清晨,随即又拔高了一个分贝:“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还我相公命来!还我相公命来啊——”
“杀他?某还不屑。”一把年轻却老成沉稳的男声传来,“还有,杀人与否自有衙门定论,你一妇人如此行事,小心某告你诬蔑,按朝堂刑罚当关上几日以儆效尤。”
男子的威慑似起了作用,妇人拔尖的嗓音戛然而止。
透过层层的人群,刚好透出一道缝隙,让楚轻看到了哭天抢地的妇人——刘二浑的婆娘刘许氏。
死的难道是刘二浑?
好歹楚轻也跟着师傅出入过几次龙门镇,自是知道刘二浑是镇上有名的混混,仗着自己的叔父是龙门镇首富刘家的家主,所以在龙门镇里插科打诨无恶不作,喜赌博,把家底都输没了,后来刘家的那位老爷干脆也不管他了,放任他自生自灭。刘二浑却是借着刘家的名头开始骗吃骗喝,可因为他有靠山,倒是也真没出过什么事。
楚轻当即就决定管了刘二浑这件事,光是他姓刘跟龙门镇刘家有关这件事,就足以让她插手了。
她正找不大由头去调查刘家,这不就送来了吗?
只是她要怎么验尸,却是个问题。
师傅刚刚出事,还是被用那么脏污的手段污蔑,众人躲她都还来不及,不过楚轻倒是在人群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衙役的头头崔大头。
她想了想,走了过去,也不出声就站在人群外往里看,崔大头几个衙役都没拦住那刘崔氏,他们虽然是衙役,可挡不住男女有别啊,也不敢真的动手,否则以这婆娘不管不顾的架势,能把他们给骂得连个底裤都不剩。
崔大头愁得头疼,突然头一偏就看到了人群之外的楚轻。
毕竟在一堆歪瓜裂枣的糙汉子映衬下,楚轻那就是一株白杨,怎么显眼怎么来。
青青翠翠的,就跟一棵小嫩葱似的,模样俊俏白皙,招人得紧。
崔大头眼睛顿时就亮了,实在等不了衙门里的仵作了,一把把楚轻给拉到了尸体旁:“楚小哥来帮个忙,给验个尸……”
楚轻敛了眼,不动声色:“崔大哥,这不合理,我是仵作,但还没有得到县太爷验状是不能随便验尸的。”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谁不知道你得了跛子张的真传,跛子张那么厉害你还不……”崔大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扇了一下自己的嘴,可挡不住话已经说出口了,只能硬着头皮干巴巴笑了笑:“哈哈,楚小哥帮个忙了,这刘崔氏说这位公子杀了她汉子,道是昨个儿他们跟着这位公子起过争执,他还打了她汉子,晚上她汉子就没回家,可明明我们亲见这刘二浑是溺死在河里的啊,只是刘崔氏一直如此不依不饶的,我们恐着刘家的势力,所以还是劳烦楚小哥你赶紧给验验,大伙也好给县太爷与刘家一个交待啊。”
若是普通人,崔大头直接给弄衙门去了,可偏偏这两位公子可是贵人啊,他前两日可是在衙门里亲眼见到县令大人给他们恭恭敬敬端茶送水什么的,这万一要是真得罪了,别说是他了,连县令大人恐怕都……
崔大头说话的当头,楚轻只感觉一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她抬起头直接看了过去,那年轻青袍男子,正用审视的目光瞧向楚轻,看到她看过来,似乎挺诧异,“你是跛子张的徒弟?”这倒是凑巧了,他这边刚打听到清水县最出名的仵作就是跛子张,他还没找到人,这跛子张的徒弟倒是送上门来了,那就且等他瞧上一瞧这跛子张的徒弟可否有真本事。
“这位公子认识楚某?”楚轻淡淡地扫了眼青袍男子问,不解他看到自己为何露出这般神情。
却见青袍男子已经敛了脸上的表情,沉稳颌首:“听闻清水县最出名的仵作就是跛子张,某好奇罢了。”
楚轻也不甚在意,只是略微一颌首,算是应了崔大头的求助。她肩膀上正好背着跛子张的仵作箱,楚轻轻轻掀了掀眼睑,睫毛飞快地颤动了下,崔大头不经意看过去,觉得这楚小哥长得真的比小姑娘还俊儿,探过头问:“楚小哥,需要哥几个帮什么忙不?”
楚轻蹲下身,点点头:“劳烦崔哥给记下验尸单。”
“行行,这个还是可以的。”崔大头连忙应和。
楚轻轻“嗯”了声,打开仵作箱,里面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与先前的凌乱完全不同。
仵作箱一共有三层,最上面一层放了验尸用的薄刀、镊子、短锯、缝合针、纱布;中间一层则是验尸单,干干净净的一叠,是翠悦轩上好的宣纸,跛子张的俸禄最烧钱的大概就是这些他一笔一划记录的验尸单了;最下面一层则是放了苍术、皂角、姜、醋以及火折子。
刘崔氏看得楚轻开始验尸,双眼紧紧的盯着尸体,抓着年轻男子的手也不知不觉松开了。
楚轻拿出一片姜含在嘴里,净手之后,随后用火折子在尸体旁焚烧苍术皂角,把这些做完之后,她这才开始观察尸体的表象。
同时边说边让崔大头记录:“男性尸体一具,尸长约五尺三寸。衣衫完好,并无外伤,腹部肿胀,按压内有积水,嘴角有蕈状泡沫。前胸两侧见深紫色尸斑,后颈有稍许尸斑痕迹,指甲缝有稍许絮状物,推断死亡时辰为昨夜子时三刻。”
楚轻话音刚落,青袍男子适时开口道:“彼此,某已经安歇在贵县最大的客栈里,客栈的掌柜伙计皆可作证。不知如此可洗脱某的嫌疑?”男子的目光落在楚轻身上,并未露出半分担心,反倒眸仁锐利沉稳,多了几分考量。
楚轻头也不抬:“这是衙门捕快与大人的事,问楚某并没有用。”说罢,并未受他的影响,她检查完尸体的表面,用薄刀切开了尸体,观察内里是否有伤,不多时站起身,继续让崔大头记录:“腹部积水,并伴有泥沙进入肺部口鼻,全身浮肿,初步断定为溺水而亡。”
她话音一落,刘崔氏嚎啕了起来:“你怎么就断定是溺水而亡了?你看我汉子这身上,青青紫紫的,一看就不对劲啊,更何况我家汉子他会水啊!会水啊!绝对是被他们给打死的,然后再抛下水的啊,天杀的啊,这还有没有个天理了啊,冤家啊,你死得好冤啊。”
“刘崔氏!”崔大头头疼,怒嚎一声:“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专门跟刘二浑估计惹事,让事主打上一两下然后坑人家银子,你要是不服,看我崔大头不把你送进牢房关几天!更何况,什么青青紫紫的,你少夸大其词,连我都知道那只是普通的尸斑罢了!”
他这么一句话落,刘崔氏跟定住了一样,没嚎出来,打了个嗝,抽抽了起来,却也不敢再闹事了。
楚轻等四周又恢复了沉静,才缓缓扫视了一圈,把众人的神情看入眼底,目光落在一处时,敛了敛眉角,这才重新看向崔大头:“她说的话,也不是全无对的。”
“啊?”啥?崔大头一脸懵逼,没反应过来。
“刘二浑的确是溺水而亡,可溺水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不小心溺水而亡;还有一种,却是外力胁迫他‘溺水而亡’。”楚轻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刘崔氏再次热血沸腾了起来,刚想嚎,被崔大头一眼瞪过去,憋紧了。
“楚小哥,你刚刚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崔大头一脸茫然。
什么叫做外力胁迫溺水而亡?感情还是他杀?
“不排除他杀。”楚轻轻合上仵作箱,站起身,朝着青袍男子看去:“不过刘二浑临死之前却是在杀人者身上留下了一些讯号,若是这位公子真的想立即排除嫌疑的话,就把你的手伸出来吧。当然,大家也把手都伸出来。”
“这是?”崔大头一愣,围观的众人则是瞪大了眼瞧着楚轻,这也太儿戏了吧?
楚轻敛下眼:“刘二浑若是他杀,死之前必然会挣扎一番,所以很可能在死者的手背上抓伤了痕迹,所以,崔哥先检查一下这些人,若是手背上没有伤痕,那就可以直接排除了。”
众人一听这,顿时松了一大口气,他们手上铁定没伤口啊。
于是为了洗脱嫌疑,立刻都伸出手让衙役检查。
楚轻跟在崔大头身后,一个个看过去,青袍男子盯着楚轻,眼底闪过一抹趣味,伸出手给她,摊开的掌心与虎口处有一层茧子。
楚轻目光扫过那薄茧,朝青袍男子多看了眼,不动声色地压下心底的疑惑,只轻声道:“刘二浑的死,与果真是与他无关。”
青袍男子眼底有微光暗动:“那小哥可看出凶手到底是谁了?”
微信篇幅有限,后续内容和情节更加精彩!
(扫码继续阅读后续精彩)
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