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提云积】自觉
描绘与描述虽一字之差,而对散文处理来说,却是两种相隔渺远的路径。描绘的后面,往往掩藏着写作者本人的野心,此处的野心与某种宏大的社会学理念相联系。即使是面对一山一石、一草一木这些元素,也要勾勒出与家国、与社会相对接的因果关联,以此指点江山,以此挥洒意气。提云积的这篇文字走的是描述的路径。作者恪守着“我看到什么,然后忠实地记录它”这样的原则,在精确性上可能远不如福楼拜,不过在味道上却是福楼拜式的。提云积的场景叙述有效地避免了这个陈旧的泥淖,同时,也很好地表现出新散文文体的一个特点,即物象并置的处理手法,物象之间没有主次之别,只是因为镜头感的推进,而有远近的不同。这个时候,写作者如同提着手提摄影机之人,通过自我的在场,一一激活所看到的物象。
——主持:楚些
自觉
所有的故事从一座塔开始。
他与他们签订了君子之盟,盟约仅凭口语,无文字传世,只是后人的虔诚与谨慎的记录。我是阅读者,字里行间能感知到他的威势。当然,他的威势含了慈悲,关怀,安详。他寄希望于他们能达到自觉,对他的善意不假丝毫的疑虑,他的胸怀畅达,世人却不能解。
一片亘古平原,介于河流之间,肥沃、丰饶。一座繁华都城,安居了他们。粮食可以自足,风物可以放眼。子民生活安稳,繁衍生息;动物欢跃,自建王国,与人类各自祥安;植物开花结果,描摹春去秋来。
平原的风吹过很多年,大河的水浩汤过很多年,世人的心磨砺过很多年。风吹着吹着不见了踪影,水流着流着归了大海,心磨着磨着就变的残缺。贪婪及一切欲望开始萌芽。他们开始想建一座塔,以避难的名义,试与天齐,或誓与天齐。这是最初,也是最原始的改造自然之举。
现世的我们不能洞窥他们所居时代的富足与发达,也不能描述其时的浮华与骄奢。总之,塔层层堆积,高可比浮云。他知道他们想到天上来,这是忤逆了他的旨意。天与地,神与人,遥视可及,却不能达。惩治的手段简单,隔阂了他们的语言,心也变得遥远,头脑走了不同的陌路,都做鸟兽散。塔还在,传世的书本里的记载,尘世不再。
故事极简,后世的阅读皆明了君子之盟的履行只是靠他与他们的自觉。现代哲学为自觉定义,其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人的基本人格。很难想象,也不难想象,如果人类放弃了自觉,单纯的依靠外力强其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其所承受的心理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承载其的社会又会是怎样形态。
他给我说起自觉的时候,是在一个下午。对于自觉的理解,凭籍自己不甚醒知的大脑,感觉应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过程。一个点是起点,一个点是结果。过程是自觉的渐趋朗清。当然,自觉一词每人的理解不同,我后来求证过多人,与词典的解释有出入的答案很多。此时,他给我说到自觉无关土地的生存状态,只是一次游历,他所说的自觉偏向于结果。游历的目的地不远,就在村庄后面的海边,海是渤海,此处因为居莱州地域名莱州湾。
聚会是他工厂里的工人发起的,工人们晚上去海边烧烤,作为一厂之主,他也受邀参加,他与儿子一起去,自家的皮卡车,车厢里装了啤酒及一应烧烤用具,工人们拼车,一行二十余人,傍晚时分到了海边,男性工人支架烧烤炉,点火,安装餐桌,女性工人打下手,准备烧烤用料,分拣餐具,收拾停当,炊烟升起,杯盏满盈。坐具不够,男性工人都有了自己的马扎,女性工人有的站着,有的四处寻找石块充当临时坐具。他做为一厂之主已经有工人给他在餐桌的主位上安置了马扎。此时是一个看点。他把自己的马扎让给了女性工人,自己去寻来一石块,铺上从啤酒箱上撕下来的纸壳安坐。他的儿子效仿他,也把马扎让给了女性工人,那些女性工人客气的谦让着。后来,那些男性工人都把自己的马扎让给了女性工人,有的寻石块,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他说这就是自觉。这是古人说的“见贤思齐”,也是古人说的“德不孤,必有邻。”从一个小马扎看日常生活习惯,男人在家里是主导地位,从未想过女人在家庭的位置,生活的一些细节带到社会上来,就会看出女性居家的从属地位。他说,他不喜欢说教,身教是最好的行为。他的举动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儿子,还影响了工人,想必他的工人从中受到启发,也会去影响别人。这是自觉的延续。他还说那晚烧烤结束,没用他的身教,工人们都自觉的把垃圾清理干净。
他因了经营自家企业的需要,走过许多的国家,产品出口到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看到外国人的生活细节,皆严谨、节制。比如车子与车道,行人与车子,男人与女人,甚至于说到了人与动物,。我说到这是不是国外有健全的法律使然,才使他们的生活状态井然有序。他不置可否,他在国外的游历只是走马观花,不能深入的领悟其中的教义,只是看到一些表象,或许待的时日久了也会有不同之处,也未可知。
去他的工厂秋日刚始,工厂在村庄的北面,紧挨着村子,目测占地有五六亩的样子,工厂的大门向东,门前是一条穿村而过的村路,向北不远便是一条省道,省道向东连接着一条国道。过了门前的村路便是一处空地,空地向北相邻的是他的另一个车间。由此向东便是一处更大的空地,空地向北,向东则是即将成熟收割的玉米,大豆,空地以前也是耕地,也生长各式粮食作物,现在只有空地西南角种植了几垄蔬菜,它们皆旺势生长,暗绿色的白菜还没有卷心,呈开放的姿态直面天空;萝卜、芹菜枝叶婆娑。它们在此,构建了泥土的养育功能是多么的强大。
从去年开始,他把这片土地从本村村民手里流转过来,准备建一个更大的工厂,我们巡查到这里时,他正在向这里运送土石方,给他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他没有继续施工,我们给他讲明如果办理用地指标的流程,他说想想办法,后来再经过这里,看到土地空置,也问询过他,他说正在办理。他的用地指标有无办理下来并不得知,2014年度的卫片执法检查却走到了前面,这块空置的土地,以及土地上堆放的沙石被卫星清晰地勾勒出来。这里做为地级市的督办清理压占项目,列于重点监督检查范围。这也是我和同事来此的目的。
这是第二批拆除(清理)耕地非农化项目。这之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批,第一批相对比较顺利,违法占地行为规模小,大多是一些临时搭建,临时压占,易于清理拆除。从开始进行卫片拆除(清理)之初,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是由易到难,由点带面,依次推进。不知道与他前面说到的“自觉”有无相通之处。
他的阅历注定他不是一个难缠的人物。在我们来之前,负责人对他曾有过一次约谈。大体讲明政策与法律,他不做辩解。后来听负责人说起他,说他是开明的人,能分清形势,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意人,或者不是一个滑头的生意人。清理压占也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我和同事比较庆幸,他在此处的清理压占行为由我们来做监督。我们只需要给推土机与挖掘机司机讲明工作步骤,应如何清理即可。
堆积了近两年的沙石土堆已经长满荒草,时至深秋,荒草几近衰败,枯黄的叶子中透出些许绿意,终不是春夏之时绿的肆无忌惮。我们过去时却惊飞了在荒草里觅食草籽的一群麻雀,它们应该是属于一个家族,翩然惊飞时看出这个家族的庞大,有上百只的样子。起初,它们肯定是被吓着了,惊飞时毫无章法可循,阵容杂乱,叽喳有声,忽而东西,忽而上下,在空中绕了几个圆圈后,在一只麻雀的带领下纷纷落在东面的玉米樱穗上,是否是在侦知我们进一步的行动,不得而知。俄顷,一只麻雀冲向天空,一声鸣叫,其他的麻雀跟着冲飞起来,几声呼哨,在土堆上空打了一个旋子,迅即降落到空地西南角的那片菜地里。想必麻雀们对于饱腹的草籽尚存丝丝念想,那片荒草曾经是它们的乐园,有温饱,有安逸,还有不愿舍弃。
不愿舍弃的岂只是它们,我想应该还有他,只是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舍,他的认知告谕他必须配合我们的工作,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铲车和运输车辆开了过来,机器轰鸣、烟囱冒着黑色的油烟。土堆很快的撕裂了一个口子,湿润的泥土气息冲了出来,我能闻出气息的慌乱,它们呈集团仓皇奔逃出来,瞬间包围了我。它们被禁闭的时间太久了,久到忘记了它们泥土的身份,它们的生机被人为的禁锢,一旦得到释放,它们此时的欢悦谁能得知?
一种褐色带了油亮的光泽,在泥土气息的裹挟下一并冲了出来,光泽带了诱惑,我知道这是植物最希求的光,与太阳光不同,它能照亮泥土内心的暗夜,如果它们是一片泥土,会是生长什么样子的庄稼,只能是由我信马猜想。
空地东面的玉米行将成熟,路北是叶子逐渐萎黄的豆秆,太阳光暖暖地照射下来,择一处比较干燥的田垄随意安坐,背依着玉米形成的屏障。随手扯了玉米须拿在手里揉捻,玉米的清香气息,夹杂着源源不断地从玉米地里窜出来的野草的气息混杂在一起,恍然觉得这就应是田野独有的味道。此刻,我只想静静地呆在这里,用心感知它们给我无边的安宁。祈愿面前的空地能赶上不停行走的季节,如它们一般,用成熟,以及丰收还泥土最本真的样貌。
时久,他来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稍做歇息。办公室在路西的厂区里,从外面也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就是村民普通的住宅。一张红木做的茶桌围坐了三人,他,我,我的同事,我们俱不做声,对于面上的话题前面已经几乎说透。他麻利地冲泡着茶水,有一瞬,我竟似听到小溪从春天的泥土上流过的声音,水汽从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升起来,刚描摹出一段曲线便没有了影踪,独留了春日的气息,让我恍若置身在盛大的春日里。下午的阳光已经变得淡漠,有光从房子南侧的窗户穿进来,自顾扑在屋内的地面上,没有了热烈,只是几片碎缕,光线淡黄,似乎为了无视我们的存在,自顾静寂的照着面前的尘世。房子南面是一个狭长的院落,靠窗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已经高过窗户,树叶绿中透着墨色,石榴还没有开裂,只是一个浑圆的果实,泛着清淡的光泽,如一只硕大的眼睛,沉默中夹杂了疑问面对我无声的观望。
屋内氤氲着藏香气息,藏香的气息该是从里屋传出来的。在这间屋子的里间供奉着一尊财神像。这间屋子并不陌生,去年因为他的非法占地行为多次进来小坐,也知道主人的习惯,每日上香,日日祈祷,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自觉行为。此时藏香掺和了茶香,浓烈、清淡互为交杂,竟使脑子放缓了运转速度,时间与世间的美好应是如此吧。不思不想,忘却纷争,忘却伤痛,或者是忘却工作的疲累。生活的各种繁忙、混乱、不易,都在此刻得以放下,只要一点儿光,一点儿香,一点点儿的清心寡欲。
室内墙壁悬挂了几幅字画。钟馗出游悬挂在墙壁的东侧墙上,钟馗着红袍,束黑腰带,目瞪欲裂,手舞宝剑,足蹈虚空,面相不足以刻画,观者的认知决定了钟馗相貌的恶与善,陋与帅。蝙蝠绕身,一只蝙蝠在钟馗的剑柄上停留。此时我单纯的以为这是另一个世界执法者应有的形象。西面墙壁是一帧清人进士张自超书写的条幅,“明月照积雪,平畴交远风。”应是张的真迹,以前多次观瞻,不识真况味,只觉语句与含义的精妙。后来查了百度才知是一副拼凑的联句。一为谢灵运的《岁暮》,一为陶渊明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各取其一,意境便大不同。雪夜,雪野,清冷的月光无边无际的挥洒,月光下的雪野,雪光迢遥,夜在雪光的尽头,风从未知的宇宙深处喁喁独来,月光下的村居,一盏淡黄的灯光,透射进雪地。冷与温,寒与暖,层次分明。一“照”一“交”,时光任意纵横。纵可涵盖,横可无垠。当然,这是古人的意境,今人识得此中况味须得不着边际的想象,没有古人真实的眼观,形象的描述。这也是自觉,是古人的自觉,自然自得,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
茶过几盏,他说到如何品茶,不识茶味如我者,浑然懵懂。如何品茶程序繁杂,要掺杂进个人的感知,这点感知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真况味,早年喜欢一首箫曲《苦雪烹茶》,开曲是几缕清音,清是相对,是物我两忘的意境,是自我的慎思,是天地之间的独行者,这清便生雅,生思,生定。接之便是悠远的长调,远到无边无际,远到可以孤寂,远到周身可以随处安歇。如此者,必有闲适之情心,当下芸芸众生,极难再寻此雅致,熙攘碌碌皆为欲利往来。
屋外天光开始晦暗,茶味渐寡,工人陆陆续续的下班,我们也该回程,告诉他,明日我们再来。他送我们出来,在大门处跟他握别时,竟发现了大门南侧种植的几株柿子树,它们还不是一棵大树,它们还小,还不足以撑起一树风雨。它们做为景观植物于此,已经失却了早年寄予它们做为经济作物的期望。进门的时候没有发觉它们的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柿子在渐暗的天色里变得明亮才引发了我的注意。柿子累累,在秋风里散发着清暖的色调。这必是泥土在盛秋时所寄望于的色调。在我的感知里,它们应该属于田野,一爿不大的果园,柿子、苹果,或者是其他的果实类作物,在秋天的眼眸里,它们各自祥安一隅,用心描摹秋天的各种姿彩。
一个下午的工作量,面前这片被压占的土地已经开始有了原始的轮廓,夕阳下的泥土依旧静默,看不出泥土的喜悲,秋风开始追逐遥坠的太阳。
回到单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另一个组的同事还没有回来,不能先走,只能是等,也不能闲坐,。
同事们回来时,外面的天光完全归于黑暗,马路对面楼房的霓虹灯开始闪亮,它们勾勒出整座楼房的外形,闪烁的霓虹灯如同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贪吃蛇,首尾相连,一个吃掉一个,色彩不断变换,楼房隐在霓虹灯炫目的光线里,它们原本的样貌被强势地剥夺了。疾驰而过的车子,带动空气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回来的同事说他们遇到了阻力。下午的时候,他们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去了当事人非法占地建筑的现场,当事人和他们见面后只一句话,我有精神病,你们看着办,再没有其他的言语。
非法占地建筑与前面说到的他的非法压占,有相通之处,也有着本质的区别。相通的是当事人的行为都对土地造成了非法侵害行为。不同的是非法压占对泥土造成的危害性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耕种,非法占地建筑已经形成事实,是一种根源性的破坏行为,即使是能恢复耕种,受损的泥土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彻底的复原,如同一个人破损了元气,想达到赤子状态,必要经过极长的保养时间才行。
当事人的非法占地建筑早已被我们的日常巡查工作发现,后来的卫星图斑也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实际存在,我们按照法定程序对其进行立案查处,也是两条处罚条款:罚款,自行拆除。在一个规定的期间内,当事人并没有按照处罚决定自觉履行其当遵循的义务。,裁决书的内容大致是给当事人一个自动履行期限,如果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自行拆除,交由地方政府强制拆除。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决书都提到了自行拆除,不管是法律,还是代表法律行使职权的机关,首先是都想到了自觉,自觉履行义务,自觉履行法律的规定。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强制执行,由政府部门组织强行拆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谁都不能判定当事人说的精神病是真是假,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后发事件,谁都无法得知。
回程时,近子夜时分,进得家门,懒得洗漱,倒头就睡,一夜酣眠。
第二日清晨,昨夜的星光还在,我们已经出发,一路无话,已没有再多的话语,所面对的状况已经对我们的思维神经造成了疲沓。临时调整工作思路,大面上统筹,易点不再专人督导,,我和同事去了另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有一株六百余年的黑檀树,在我到这个乡镇工作时,听同事们刻意说起这株树的来历,我也曾做了刻意的寻访。这株树出现在这里得益于这个村庄的始祖自四川启程时的一个举措。六百年前的移民政策,是皇权的高度遵守,没有自觉,是严苛的统一,他们的始祖不能违拗。从门前的黑檀树下抓一把泥土,在其始祖矮下身去抓这把泥土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或许是跪了下去,甚至于是匍匐在地,双手捧起面前的一把泥土,这把泥土从故乡的肉体上生生地剥离,那种痛已经痛到了心里,这种痛感足以麻木一个人的身心,他不会想到六百年后,这把泥土会孕育了一个传奇。
我曾经想过,那也应该是一个秋日,一个深秋的日子,如同走过的许许多多的日子一般,本没有丝毫的传奇,田野的庄稼该熟的时候就得熟,该收的时候就得收。黑檀树应该是遮天蔽日了,就像现在的这棵黑檀树一般,树冠浓密,桠柯虬曲,枝叶纷披。六百年的黑檀树已经是一个传奇。传奇的本身,是其始祖的那把泥土,泥土里暗藏了黑檀树的种子。泥土不但携带了故乡的气息,还暗藏了故乡的生命。此时的黑檀树严谨的保持了与故乡黑檀树的一致性,这也应该是自觉吧。是植物本身特性。从古至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是植物的自觉,这种自觉是黑檀树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不会出现丝毫的偏差。如果他能想到,他所破坏的土地是他的始祖从故乡剥离的血肉的延伸,他还会肆意妄为吗?!他的始祖选择这里安居乐业是因为这里有肥沃的泥土,可以生长饱腹的五谷禾苗,他的始祖是怀着虔诚的心态将这里作为桑梓地,那一把泥土已经在这里得到繁衍生息。
在这个村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4年,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面色黑红的农家汉子,大脸近似方圆,寸头,躯干结实,近凭外观不能呈现出其狡黠的本质。他的违法占地建筑现场位于这个村子的西南位置,在出村子的路的北面,沿路边有几间养殖房,早年是养殖鸡的简易棚子,由养殖房向北便是一爿果园,与东邻的果园连成一片。我们巡查到这里时候,是2014年初夏时节的一个上午,果园里的苹果树已经砍伐殆尽,果树根皆翻转裸露在地表上,树身不知去向,初夏时节的阳光开始煦暖,空气里弥漫着泥土湿润鲜腥的气息,此处看不到安隐于泥土中勃发的生机,每一个树根的边上都是一个泥坑,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它们的家,现在它们的家破,它们也已亡。
我不想用死寂来描述此处泥土的状态,即使是没有了果树,那些尚没有清除干净的野草还在作势努力地生长,它们的存在于火热的施工现场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查看现场时惊飞了在此处觅食果树根部虫子的一群麻雀,它们飞到东临的果园里,东邻的果园还是保持原貌,苹果花已经凋落,枝桠间安隐了一个个小小的果实,它们呈青绿色,那是一包生机,如果是秋日来临,那一包生机该是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描述的甜美。现在它们都努力地生长,好像要把西邻果园的那些生机一起描摹出来。假如此处没有这样的砍伐,这一片泥土也应是繁盛如初。面对现场只能是假如,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果园的四围建了院墙地基,在院子的东北角还有一处新的建筑现场,建筑尚未成型,仅一米多高,建筑框架呈方形,根据工作经验推测应是一处锯房,用于安装一种大型切割设备。这里盛产大理石板材,一些大理石荒料被钢锯切割成大理石板材毛料,然后再经过打磨,就是光可鉴人的用于装饰用的大理石板材。
他没有过多的话语,吐语嗫嚅,从谈吐上看不出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板。我承认,有一刻,我对他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他的不做声张,甚至于几个细碎的动作都刻意的说明他只是一个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农人。他给我们的解释是准备养猪,现在是建库房,准备存放养猪饲料。以前是果园,因为品质老化,已经没有了市场,早年与村委签订的合同还没有到期,只能是改做养猪。让他提供出和村委签订的合同,他以老婆不在家,拿不出为借口拒不提供。我们现场电话询问了这个村子的村委主任,村委主任推做不知他的行为告罢。
多方面的信息判定他这是明显的谎言,给他详细解释了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后果,也给他列举了违法占地建筑所受惩罚的事例,有的违法当事人他还认识,我们着重强调了将要受到的处罚结果,不但是要罚款,还要拆除。他不辨所以,只是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所有的解释与他目前的行为无关,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我们的解释于他并没有任何的关联。为了不出现续建现象,现场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施工,撤走施工设备和人员,听候处理。他还是刚开始给我们做解释的样子,面部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们都以为这是法律的震慑力,会迫使他的违法占地行为有所收敛。当然,我们也不敢妄作定论,毕竟这是职责所在,不敢有丝毫的麻痹思想。
事情的进展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他果然建了锯房。我清楚的记得,那日我们再去这里巡查时的情景。看着他将要落成的锯房,我们的巡查负责人大动肝火,他好像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直陪着小心,这次他的老婆在家,也过来帮衬说着讨好的话。我离开他们纷乱说话的场地,拿着相机围着锯房寻找角度拍摄现场照片。在我拍完一个角度,准备选择一个远景时,回头看到他也离开了那个纷乱的场地,只留了他的老婆还在向我们的巡查负责人解释着什么。他独自向我靠了过来,我拍摄完违法占地的远景照片,他已经走到我的身边,一只手极快地伸向我,我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我脑子瞬间闪过他是不是要对我动武,我晃过半个身位,侧身对着他,我的声音不大,但应该是严厉的,“别靠近我”。他尴尬地伸开握紧的手,那里是一张卡片,闪着红色光泽,此时的红光在我眼里竟是隐晦的,如他的脸色,是被我喝止举动后的懊羞。他当然不知道我隐于内心的恨意。我定定地看住他,你离我远点。我感觉得到,那几个字是从我的唇边一个一个跳出去的,它们具有无形的杀伤力,同时刻可以肯定的是我的面相是冰冷的,从他讪讪地表情里能感知到我面相的寒意。我不能做到和颜悦色,脚下的这片泥土,踏上的每一步,我都试图感觉它的每一缕伤痛。他用那么多的谎言掩盖他的恶行。他不以为这就是犯罪,土地在养育世人,也养育了世人的无知,甚至于背负了世人的罪恶。这几年见多了她的伤,她的痛,独独没有听到土地的呻吟或者是哀鸣,恰恰是泥土的沉默,才让我感觉痛彻肺腑。
这桩违法占地案子,从开始我们就忽视了一个人物。他的老婆,此处有必要多交代几笔。近五十岁的农村女人,看面相或许能再大一些,生的黑且瘦,戴一副黑边无框近视眼镜,脸颊窄而尖,颧骨略高,给我的感觉不是鼻子架住了眼镜,而是得益于颧骨。眼光频闪,不能专注于和她交流的人,她的嘴唇薄,泛着青紫色,牙齿错列。她说话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嘴唇的翕动,语速能配合着面部表情时快时慢。身骨略瘦,不是单薄,是硬,是一种由身体内里生出的硬。因为他们的违法占地,以后又见过几次,她给我的感觉一直没有改变。
事实已经形成,现状摆在这里,他也再不能自圆其说。再次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其下午到分局做一个问询笔录。
当日下午刚上班,从办事大厅的窗口看到一辆黑色别克车开进了院子,别克车在门厅前急速地划了一个半圆,黝黑的漆色在太阳底下晃出一道耀眼的光斑射进了办事大厅。车子在院子里停了好长时间,两侧的车门才打开,他,他的老婆——那个黑且瘦硬的女人,一起下了车。他走在前面,他老婆在后紧随,他不时地回头和老婆交待着什么。
他坐在同事的面前,对于同事做的相关问询,他依旧嗫嚅,要么就回头看一眼他的老婆,他老婆再对同一问题重新做一次说明。笔录做完,虽说是向他了解有关情况,基本上是他老婆做了全部的说明,违法占地行为触及不多,说的最多的是他们家的窘境。儿子正在上高中一年级,眼睛因视网膜病变严重影响到视力,可能会有失明的危险,去了国内许多知名的眼科医院求医,效果一直不明显,花费已经是天文数字,能不能不处罚,或者是少处罚。她站在男人的身后,手掌心里一直扣着一块纸巾,配合着她的说辞,不时地摘掉眼镜,擦拭着看不出落泪的眼睛。同事表现出无奈,法律的刚性谁也不能逾越,只能是让他们先回去,处理的进展情况会及时与他们联系。并再次叮嘱,不要再组织施工,最终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谁也不能代替,他们皆连声应诺。
有时候我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是从我内心生发出来的。怀疑法律的刚性,由法律的刚性延伸到人的柔性。人的柔性该如何诠释?是承压的心理状态,比如:不管不顾,听之任之;还是一种试探中的小心翼翼,比如:蚕食、观望中的渐进;再或是一种盲目的挤压,比如:从众,攀比。等等,不一而足,诠释的因果之间答案应该有很多,具体是哪一个能突出一些,具有代表性,谁也无法界定一个确切的答案。
日子平白无奇,流水一样。他违法占地案子的处罚程序按照每一个时间节点,一步一步,缓缓而来。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照例不听劝阻,下达的停工令根本不存在一般。在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前,他的锯房已经落成。我们再去的时候,锯房里已经安装了大型的钢锯,门框上系了红绸布,他用一种审视我们的眼光探问我们,我已经建成了,你们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程序没有任何的闪失,也不存在任何的漏洞,看着他的违法占地建筑成果,我们只能是等,再等一个期间的终止,。
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我们的执法,当事人的建筑进度会不会没有这么快?因为我们的介入,给当事人造成了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是法律的刚性,而是要尽快的建筑成型,使法律在他们的违建面前退步。日常和同事交流,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这么多年的执法监察工作,你看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不解。他继续说,从面上讲,我们对每一宗违法占地行为都处理到位了,这由我们百分百的立案率做为证据。但是再进一步的结果是怎样的?要求拆除的,拆除了嘛?要求没收的,没收了嘛?,而是执行力度。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自行拆除的层面,试问一下,哪一个当事人能把自己的辛苦血汗钱毁在自己的手里?多年前的执法手段明显不能与形势共进退,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自觉对不对?这个概念应该没有任何的错误,执法机关,执法者,都寄希望于当事人的自觉,在利益面前,换句话说,在当下的社会大环境下,谁能有这个觉悟?当事人没有自觉性,只能是由法律的刚性来理顺这个问题,而目前恰恰缺少的就是法律的刚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法律刚性缺失,大家都明白,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个现成的答案,无须问询任何人。你、他、我,都有这样一个答案。
后来有一天,,,来我们分局对当事人下达传票,他和他的老婆一起过来。,相信他们还是心怀了畏惧。,又是为何没有自行拆除。理由简单,那时我在场。他的老婆把儿子的情况复述了一遍,又加入了其二哥在外面帮助他们销售理石板材遭遇车祸死亡,至今没有捉到肇事者。家庭境况雪上加霜。女人的眼泪很多,,。
,听负责人回来的讲述知道,他老婆的当庭陈述,竟使一众参加人员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失声流涕。负责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午饭后,同事们都在办事大厅闲坐。片刻的沉默,唯我不合时宜。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他在我们给他下达第一道停工令的时候能停止违法占地行为,还会有今天的结局吗?肯定不会。他的家庭遭遇令人同情,这也是现实,关键这不应该是其可以违法的理由。何况他的理由我们没有问询其他任何的第三人作为印证。再假如,他的遭遇是真实发生的,可以走民政救济的渠道。即使是第三人为其做了证明,这又能说明什么?我们难道可以为其违法占地行为大开绿灯?没有任何一个法律的条款可以因为当事人的家庭出现变故,或者是其他的灾殃,授权他的执法者可以有此权利。
当所有的一切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自觉性就尤为重要,如果不能自觉,别人的提醒能引发你的惊觉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惜,他都不能做到。这是他违法占地由始至终的过程,我只是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叙述,删除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无关该问题的解决。
今天我们去他的村庄,当地政府的分管领导同行,分乘两辆车,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之前,,自行拆除,限期缴纳罚款。在一个期间内如不能履行,将授权当地政府强制拆除。这个时间段恰好与卫片执法检查相印合。
时隔一年我再次到了他的违法占地现场。从去年看到他的新锯房落成后我没有再来这里,年初进行的变更调查工作,我核查的是另外的几个图幅。再来就有点生疏,我已经不能很好地分辨他的违法占地现场。我看到了什么?高耸的院墙,敞开的大门,大门是朱红色的,和去年他拴在锯房门框上的红绸布一样的颜色。沿路的养殖棚已经不见踪影,取代的是新建的民宅,民宅在大门以东,红瓦,雪白的檐墙,铝合金的门窗,从窗户上能看到做工豪华的窗帘。我把车子停在大门的西侧,这里并不是专门用来停车的,进门的时候我看到那辆漆黑铮亮的别克轿车就停放在大门的西侧,车头向西,车尾向东。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把这里当做了停车场,我把车子停在与他的别克车相差一个车位的位置,这样也方便后面的车辆开进来。
院子里整齐地垛放着加工好的理石板材,有的已经打包等待外运,一个简易吊装铁架稳稳站在院子靠北的位置,大块的荒料堆放在锯房外面,锯房那边传出刺耳的切割声,打磨声。我看到了繁忙的生产景象,独独看不到去年的那片泥土了,看不到那群飞翔的麻雀,看不到那些被砍伐殆尽的果树,也看不到相邻的果园了,及覆盖在果园上空无尽的秋色。现在,这个大院是实质意义上的虚对天空。
我们站在大门口,根据卫片图斑提供的范围察看他院子里的情况,商量如何进行下步清理工作。他和他的老婆应该是从室内的监控看到我们过来了,一起迎了出来。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唯政府的分管领导是第一次见。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待我们开口,他的老婆先发话,你们这是往死里逼我们,你们要是敢来拆,我就敢死在你们面前。好像是为了加深她说话的真实性,又做了一个说明,她已经买好剧毒农药了,就在家里放着,光等着你们来了。
停滞,场面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我只是一名观众。他老婆的话明显的是对着政府的分管领导说的,她的目光不再游移不定,我站在她的右侧靠前的位置,也能感觉到覆盖在政府分管领导身上的寒意。已经没有了眼泪,每一个字里都饱满了恨意,是一种硬硬的恨意,这种恨里有剧烈的寒意聚拢。我感觉到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丝丝寒意从未知的角落瞬间迸发出来。我抬起头看看天上,太阳早已经升起来了,漂浮在空中若有如无的雾霾阻断了太阳金黄的暖意,这世间竟是浅灰色的。我的认知告诉我,这是秋天呀,是金黄太阳的秋天,是金黄硕果的秋天。我怎么会感觉到寒凉。寒凉是逐渐增强的。他照例不说话,我看到他的脸色在他老婆说出剧毒农药时,已经不是早前认识时候的黑红色,是酱紫色,鼻息粗重,我能感知他此时的心境已经波澜微惊。
剧毒农药是除草剂,曾亲眼见荒草在喷过除草剂以后,在极短的时间里开始萎黄,直至枯死。还曾听过医生朋友的说法,如果误服除草剂,基本没有解救的时间,除草剂的强烈致命性,让只是听到的人都会产生胆颤。他老婆竟以口服除草剂为要挟的筹码,工作还没有开始,僵局产生。我能感知到现场寒凉的气息是由弱渐盛,我们以及他们,都僵持在一个点上,时间在考量我们哪一方能在这个点上站稳脚跟,我们都在僵局中沉默。
一群麻雀不知从何处飞来,越过我们的头顶,迅疾落在那处住宅的门前,想必是那里的食物引发了它们的兴趣,它们围拢一方,拥挤在一起,头部低下去的时候,尾部抬起,喳喳的叫声纷杂,不像是在搜寻地上的食物残渣,更多的像是嬉戏,时而蹦跳,时而相向振翅扑打,它们的欢悦与我们此时的沉默形成强烈的发差。我被它们的欢悦吸引,选择从我所处面前的场景退出去。我绕过众人,在我向那群觅食的麻雀走过去时,引发了它们的警觉,它们出现瞬间的停顿,我看到它们小小的身子向下一顿,头部昂起,左右观望了一下,像是告知同伴就要来临的危险,没有号令,它们几乎一起起飞,扑棱声还在我的面前,它们已经越过东面的高墙,我知道高墙的东面还是那处尚存的果园,那里更适合它们的嬉戏,觅食,甚或是生儿育女。
我站定在那群麻雀围拢的地方,有一地的食物残渣,还有几颗黄澄澄的小米,应该是他家早饭淘米的遗漏,细微的食物,竟是麻雀的盛宴,思维出现稍许的恍惚,依稀记起一个文字的说法,称作麻雀是世间的乞讨者。其实,我们和麻雀没有区别,都乞讨与这个尘世,我们乞讨于泥土,泥土放低身躯,承载了世间的一切,只是不知,我们人类的乞讨已经是变相的掠夺与毁灭。
僵局是如何打破的,我不知道,我选择了逃避,我无法面对这种僵局,更多的是我无法面对打破这种僵局的手段。当然,僵局必须打破,那个聚焦点只能站稳一方,另一方需要作出牺牲。不管哪一方作出牺牲,土地的生存状态都令人堪忧。
在我怔忪出神的时间里,我不知道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同事招呼我开车,我才发觉,那个场景和我正在面对的场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都已不在。麻雀所遗留给我的现场是一个清冷的生活现场,另一个现场保持着刚才的冷寂,让我感觉这个院落以后还会有故事继续发生,谁也无法预知到结局。
领导们临时决定回程,我们同事三人启程去另一个督导点。沿着南北路一直向北,距离近十公里,另一个村庄,另一处现场,或许是另一处难点在等着我们。起始唯有车子发动机的噪声时时袭扰,恒定的频率,竟使我的注意力不能全部放在开车上,思想时有散涣,木呆。已经接触的当事人的态度,尚未见面的当事人无法预知的态度,发生的已经发生,矛盾明显,未发生的会是如何变数,是升级状态还是递减状态,谁也无法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矛盾的聚焦点肯定不同,每个当事人面对现实问题的处理解决办法与手段也不同。
车窗外已经是深秋的景色,路两边是由南至北逐渐走低且起伏不定的丘陵,此处的丘陵想努力攀爬过东面的山岭,山岭的另一面应该是大片的泥土吧,那里想必掩藏着无垠的旷野和平畴阡陌。近处的田垄有麦苗暗喻着泥土的生机,空旷的风在田野里打转,此时飞翔的麻雀群做了田野的主人,它们清脆欢快的叫声在清晨衬托出天光的透亮,一团淡雾正从田野里退出去,它就像是昨夜的一个谎言,当包藏它的黑暗离去,一阵虚无的风,一缕太阳的光,都能穿透它的假面。
车内的空气稍显沉闷,我的注意力更加散漫。打开车窗,田野的风瞬时窜进来,脑子得到片刻的清醒。好像是自言自语,也好像是说给我听,同事说了这场“拉锯战”最终的处理办法。那个聚焦点名义上看是站稳了双方,一方是法律,一方是违法行为当事人。院墙和锯房先不必拆除,看上级的督办力度再说,院子西面垛放荒料和板材的空地要腾出来,把地面覆土,准备明年进行种植。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只是承诺关键时候不会掉链子。当事人的说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何况他的诚信力早已经没有折扣的余地。末了,同事好像是做了一个总结,老百姓还是太老实了。
我明白同事这句话包含的意思,但不能说出来,这个意思我们都懂,它就堵在我们胸腔靠上的位置,噎住我们顺畅的呼吸。我不知道我是否保持了清醒。我与同事观点持否定的态度。这样的老百姓不老实,这是我从这一事件自开始到今日的一个总结。如果他真的老实,在他刚开始动工,我们下达了第一道停工令的时候,就应该停止施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老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然不能包含顺从,单纯的顺从会丧失了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我理解的老实,首先应该是诚实,及诚实之下的忠厚,然后才是他意,比如遵守,不逾矩,不违法。老实与职业,与年龄无关,与一个人对事物的处理方式有关。
丘陵层层下跌的落差,泥土由高端趋于低谷,这是另一处现场,位于另一个村庄的南面,紧挨着村子,用一个加工区更能说明此处的存在意义,这个村庄几乎隐在丘陵的低洼处,村庄的名字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一条沟,村庄在河沟的北面,这条河沟承载了这个村庄的所有的历史。河沟南面是早年兴盛的废旧塑料加工区。这处现场确切的位置在加工区的南端,院墙南是一条村路,隔开了加工区与种植区。越过南北长度近百米的种植区是一条更加宽阔的河道。河道早已干涸,它的存在只能证明它曾经养育了河道两岸的子民及各种植物,现在干涸的河床已经被农人开垦出来种植了小麦,她在继续承载着养育功能。
此处的田野已经近于空旷,从南面丘陵上顺势窜下来的秋风在河道这里得到短暂的缓冲,然后顺着河道的北崖冲将起来,携带了田野的气息将我们所处的位置紧紧地包围起来。田野上星罗的树木,恍惚是不知昼夜勤劳耕作的农人。也许是一捧土,也许是巴掌大的一片地,层层累积成今天可以眼观的大片的土地。一群麻雀飞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在南面那片土地上飞翔的麻雀跟了过来,它们是不是要跟定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举动。它们落在面前的这片麦地里,麦苗已经分蘖,隐隐看见垄间的泥土,旺势的麦苗隐藏了它们臃肿的小小的身体。又一阵风来,吹动顺着河道北岸随意垛放的玉米秸秆,发出飒飒的风声,惊扰了隐藏在垄间的麻雀,它们翩然惊飞,几声唿哨,飞过南面的河道,顺着爬升的丘陵,努力向南飞去,渐渐地与南面的泥土混为一体,消失不见。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天光已经不是清亮,暖色的阳光铺天盖地。现场就在我们的面前,是一处院子,院子在此处已有几个年头。他的违法占地建筑是在院子里的北侧,以前是空地,今年开春的时候当事人在空地建了一排仓库,有十间小房,高不过住宅的檐头。地貌丝毫的差别也瞒不过在高空巡视的卫星。疑似图斑核查时,根据图片的指引我们找到了这里,它所具有的隐蔽性躲过了我们的日常巡查。
今日再来,当事人不在,来之前已经给他通过电话告诉他我们要来现场,请他配合工作。现场给他电话,提示已经关机。再之前,我们已经对他的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了调查取证,立案,下达处罚决定。法律程序按部就班,逐步推进。他避开了我们,以为就能避开法律的惩处,这是他单纯的想法。现场电话请示领导,叮嘱我们先去其他督导点转转,这里他们联系该村村委负责人,责成他们联系当事人。
后来,该处现场我们再没有去。当地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联合相关部门对不能配合清理拆除的违法占地的当事人的加工场所进行断电断水的行政措施。再后来,故事继续发生。
此处现场的当事人拒不配合清理拆除行动。政府通过电力部门向上级请示后对其用电行为进行限制。一条正在流淌的河流如果进行截堵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决堤?还是枯竭?还是重新冲出一条河道?
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我没有记录。只是清楚的记得是一个周一的上午。单位负责人带领一名具体分管的同事去政府对接接下来的工作。毕竟,在政府部门采取断电断水措施后,有的当事人开始醒悟,不管是被动,还是不情愿的行动,总之开始有了行动。此处的当事人也有了行动,确切的说是当事人的老婆有了行动。
现场应该是激烈的。后来听同去的同事讲起这个过程,我还是能感觉得到内心的战栗。同事们去政府时,当事人的老婆已经坐在党政办公室了,随身提了一个包装袋,沉甸甸地,包装袋陈旧,谁也没有认真注意这个包装袋的独特之处。政府包片的工作人员来来去去的给她讲解当前的工作形势,她的执意,她的坚守,注定她的行为走向极端。
办公室在二楼,正对着上楼的楼梯,楼梯是双向的,二楼的走廊因为低矮狭长,光线暗淡,给进入的人造成逼仄压抑的感觉。不知道她的态度是不是受了这种氛围的影响,在她得不到明确答复恢复用电的意图时,她的声音骤然拔高,是近乎疯狂的呐喊。她冲开劝解她的工作人员,打开办公室的门,探手从随身携带的包装袋里拿出一瓶液体,奋力砸在楼梯的扶手上,瞬间一股浓重刺鼻的农药气息在二楼蔓延开来。同事们在讲述这个经过时,几乎忘记了换气,一口气讲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听的正入心,同事的关子打住。我的思维是一条急速奔腾的河流,被人为的拽住,我感觉到了窒息。
同事说,那些乳白色的液体随着玻璃瓶子破碎迸溅后,遇到任何的物体都冒着白色的气泡,后来这些液体在地面形成一条浊流,顺着楼道缓慢地向楼下流去,它们像是要带走这个释放它们的女人的所有的愤怒。
这个女人继续探手包装袋,在她身边站立的包片工作人员急忙过来和她争抢,女人转移目标,动用了她的牙齿,她猛然低下头,张嘴咬住包片工作人员的手腕,工作人员吃疼放开了争夺包装袋的手,她没有丝毫的犹豫,探手从包装袋里又拿出一瓶液体,所有的人以为她会把这瓶液体效仿第一瓶砸向一个随意的目标。她拧开了瓶盖,作势抬起头,像要喝掉一瓶饮料一样的动作,就那么随意的仰起头。同事惊讶的吆喝出来,不知道是同事的吆喝使她受惊得到清醒,还是液体的气味不能使她抱定喝下去的决心。总之,她没有喝,只是一个作势的动作,她的头仰着,一只手拿着那个液体瓶子,另一只手的包装袋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空出来的另一只手用手接住从玻璃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抹在自己的下嘴巴上,站在另一边的工作人员没有看清她的举动,抱住被她咬痛的手腕向她撞去,以阻止她进一步的疯狂行动。随即公安干警赶到,这将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时间继续前进,期间有不同的消息偶然传来。她被刑拘,准备判刑。在经过一个期间之后,。,给当事人下达传票。我再次见到了当事人,细数与当事人见过五次面,这次是第六次。前面五次都是与其非法占地的有关,每一次都是一个法律程序的推进,见面的时间是每一个法律程序的推进期间的结束。今天再见到当事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情,。
他的精神状态明显的萎靡,见到我的时候,还想向我笑一下打个招呼,这宗案件从接触他开始,今天这样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笑泄露了他的内心,面部肌肉是僵硬的,他想调动唇部肌肉,把嘴角提拉起来,可事与愿违。我从我的岗位上站了起来,隔着办事柜台向他伸出手,他犹疑着,最终还是伸出手来,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极快地握了一下。
,告辞离开,出于礼貌,我站起身送他出办事大厅。大厅外的廊厅下,他站住对我欲言又止的样子。上午十点左右的阳光与廊厅支撑柱形成了切线,他就站在切线的阴影里。他左侧的小花圃里是没有叶片的女贞,灰白近于枯干的枝条纷杂错乱。事情发展到今天,都不是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愿意看到的。
在我们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后,其执意不履行,随之又下达了《自动履行催告书》,他来分局取的,我又对其讲明利害关系,他承诺回家筹款,一定缴纳罚款。我以为他能听从我的劝告,结果他一去无踪。我曾经给他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他接的,还是同意缴纳罚款,言之凿凿,我深信不疑,随即向市局申请对其开具缴纳罚款通知单。第二次电话是告知其到分局取缴纳罚款通知单,是其老婆接的,语速不疾不徐,感觉每一个字是从牙缝里经过严重的挤压迸发出来的,我恍若看到她冷寂的脸色,有寒凉顺着无形的电波穿透过来。他老婆问我,他们凭什么要交罚款,即便是现在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交,你们要抓就抓,俺家没有钱给你们。不待我给她做一下解释,电话扣掉,再打回去,再挂掉,我清楚的记得,第三次以后电话就关机了,一个上午我打了十次电话,最终放弃。
后来,他老婆大闹政府,同事讲述事情的过程时,我在心里就想到了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他老婆肯定做得出来。我想到了他老婆和我电话时的情形,我能从他老婆的语气里听出含了阴鸷气息,不仅仅是语气的寒凉。
我没有刻意的阻止他要说什么的意图,,争取有一个好的结局,不仅仅是当下的违法占地案件,还有他老婆那边的案件。他最终叹一口气,如果开始就听从我的劝告,事情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他是听了村里一些人的撺掇才做出这样的傻事的。我无言以对。他转身开车离去。
平淡的是时间,跌宕的是过往。,不知道,裁决书没有看到。他老婆是如何宣判的,也不知道,这是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我无从分心。我知道的是,新一轮的疑似图斑核查又要开始了。时间已近阳历的年底,一场风雪过后,很快就是阳历新年。新年后第一日上班,车下高速公路,晨霭还在,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多杂起来,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一只麻雀出现在我的视野,它自顾在路边蹦跳,全然不顾来来往往的车流,它是一只落单的麻雀,我们的车子从它的身边驶过,它也没有惊飞,路两边是挤挤挨挨的厂房,间或一处村路,可以看到远处的田野,墨绿的麦苗真好看。
小众,去蔽的文学力量。当代文学的别种状态,更为真实的文学中国。
小众信箱:xuanwu1972@126.com,QQ号:360144285
“小众”题字为汪惠仁先生所书。
支持纸媒(以时间为序,陆续增加中):
太原晚报、《漳河文学》、《青年文学》、《南方文学》(公众号:nanfangwenxue)、《山西文学》、《名作欣赏》(公众号:mzxszzs)、《作品》、《人民文学》、《太湖》、《天涯》、《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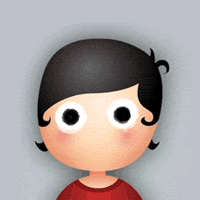
Copyright © 重庆钢铁护栏交流组